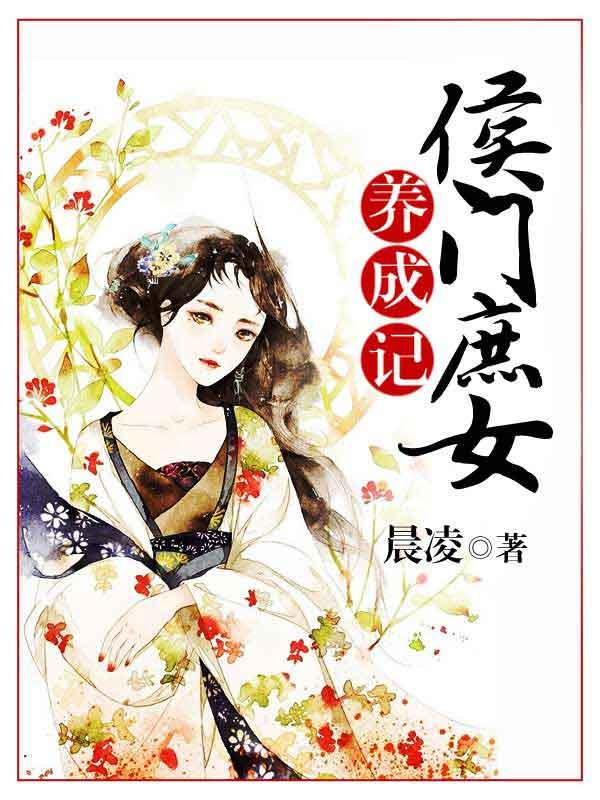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文史述林 >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商兑和补遗(第2页)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商兑和补遗(第2页)
《擎头乡里行》(〇一二)
擎头乡里行,事当逞靴袄。
楚按:按梵志零三八首亦云:“事当好衣裳,得便走出去。”则“事当”或是穿戴之义。
明按:本诗中应为“应当”义,至明。零三八首中似为“当着(有好衣)时”,得便就出门显示。“事当”绝不会有穿戴之义。穿戴虽适句意,但由句意逆推,是可允许的表述,并非词义。清黄生《义符》下:“《汉书。王莽传》:‘非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也。’师古云:‘郑重,犹频烦也。’予谓颜训是也,然得其义而未得其声。盖郑重即申重(平声)之转去者尔。”所谓“得其义”,即释义合句意;所谓“得其声”,即扣紧词语用字的形或声,这样才是文从字顺。以穿戴释“事当”即未得其声。
《使者门前唤》(〇一五)
宅舍无身护,妻子被人欺。
明按:当为“不自护”,言死者不能保护,“自”为无义词尾。
钱财不关己,庄牧永长离。
楚按:庄牧:庄园及牧地。《孟子。公孙丑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赵歧注:“牧,牧地。”《世说新语。俭啬》:“司徒王戎,既富且贵,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
明按:庄园及牧地,是物不是人,难以说它们离开主人。诗中言死者之财富,也无须特用牧地以示。《校辑》录该句作“庄收永长离”,因知第二字在抄本中不清晰,实则应校为“奴”。“庄奴永长离”则意无差爽。〇〇九首:“妻是他人妻,儿被后翁使。奴事新郎君,婢逐后娘子”。〇一六首:“有奴不能使,有婢不相随。有食不能吃,向前恒受饥。”并可参证诗意及措句。所引《世说》句实属误解。其中“僮牧”即牧僮,定语后置。否则,绝不会把区宅、僮仆、牧地并列,而将田地、水碓另列。试看任防《为卞彬谢启》:“碑表芜秽,丘树荒毁,狐兔成穴,僮牧哀歌。”正是言牧僮哀歌。
《沉沦三恶道》(〇一六)
沉沦三恶道,家内无人知。有衣不能著……
明按:“家”为“冢”之误。言所有冢内的人都不知自己的财产自己不能用了。但这个事实不仅家内,而且世人皆知,故“家”字必误。《管锥编》第三册1095页言,《全三国文》卷五。嵇康《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得无半非冢宅耶”句“冢”为“家”之误,与此正为互误之例。
《告知贤贵等》(〇一八)
憨人连脑痴,买锦妻装束。
楚按:连脑痴:极其愚笨,亦作“合脑痴”、“合头痴。”梵志诗?三五首:“杌杌贪生业,憨人合脑痴。”《变文集。燕子赋》:“燕子语雀儿:‘好得合头痴。向吾宅里坐,却捉主人欺。”’按,“连脑”、“合脑”、“合头”皆愚痴之意,故后来禅宗话头遂有“合头语”之说。《传灯录》十四《华亭船子和尚》:“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五灯会元》十八《大沩海评禅师》:”一句合头语,万劫堕迷津。”
明按:合头、合脑,连脑,无从得愚痴之意。“合”者全也。“连脑”亦全脑,今西北口语有“连相”、“连相子”说法,即全都之义。如:“车轮同轴连相子转动”。“那一些子纸你连相拿去”。“本来只须头偏一点,你却连相子偏到东面了。”即全都转动,全拿去,全偏到东。“合头”、“合脑”与“连脑”结构不同,本身都不表愚痴之意,只有带上痴字才是满脑愚痴义。至于禅僧的“合头语”却与此两属。“合”者混也,囫囵也,笼统也。“头”为词尾。“合头语”即笼统话,不着边际,大而不当。船子和尚的话头缘起,在《五灯会元》卷五中叙得清楚:“船子才见(夹山),便问:‘大德住甚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甚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非耳目之所到”,本是机锋语,即不关文字,不落言诠,船子怎会讥为愚蠢话呢?正因藏有机锋而不明显,所以投子誉为合头。他的意思本是:这一句好似笼统含混实则妙有机锋的话,弄得许多僧徒象蠢驴被拴在木橛上一样,而你算是悟解了。大沩海评禅师的话也只能是这个意思。
《旁看数个大憨痴》(〇一九)
人人百岁乃有一,纵令长命七十稀。
明按:如此标点,即直叙实况,有一人可活百岁,此则违事理更背文意,诗以七十岁为长命。句为反问,非标问号不可:人人希望活百岁,而有一人可活百岁吗?寿命再长也只有很少的人只活七十岁。诗实以“百岁”指代长生不死,如同梵志别诗所言“唱千年调”。中途少少辽乱死,亦有初生婴孩儿。
明按:诗以七十岁为寿命终点。下言“口□□口期却半,恰似流星光暂时”,即寿命短一点的活七十岁的一半,即三四十岁。“期却半”应设注而未注。下句当言亦有初生婴孩儿,“中途少少潦乱死”,即再差一等的是三四十岁以下,直至死亡的婴儿。层次非常清楚,项书将“中途”一意的下句误移为上句,打乱了层次,就难以知道“中途”是哪一段,从何处作始终,“亦有初生婴孩儿”又成为半句话。《校辑》两句次序本不误。又,项书注“少少”通“稍稍”,渐渐义。渐渐死去,于诗意无补,当校为“不少”之误,言活不到三四十岁的人不少,于诗意为长。
《各各保爱脓血袋》(〇二〇)
令身不行不修福,口至宝山空手归。
楚按:不行:当有误字。
明按:似当为“不醒”,言不明白。
《借贷不交通》(〇二二)
破除不由你,用尽遮他莫。
楚按:“遮他莫”是“莫遮他”之倒装。
明按:汉语没有“谓语。宾语。否定性状语”的词序,此“倒装说”令人难从。似可认“莫”为“麽”的音误,句言:他人用尽死人的钱,死人能阻挡他吗?
借贷不交通,有酒深藏着。
楚按:所谓“不交通”,非谓不与人来往,但不接受财物也。
明按:不接受财物与借贷不承。句当言:别人来借贷,有钱人不给借。诗即讽此。不受财物并非恶行,诗何得作讽?
《道士头侧方》(〇二三)
同尊佛道教,凡俗送衣裳。粮食逢医药,垂死续命汤。
明按:“逢”字不适句意,当有误。疑原作“并”,曾形误为“丰”,传抄至此卷又误为“逢”。句言凡俗所送者有衣,有粮,并有药。
《观内有妇人》(〇二四)
贫无巡门乞,得谷相共餐。
楚按:此首所写为下层贫苦道姑之苦情。……故此首云:“眷属王役苦,衣食远求难。出无夫婿见,病困绝人看。”下层道姑本是贫家女儿,两处艰难,无法相顾。故结云:“乞就生缘活,交即免饥寒。”渴望还乡与亲人相濡以沫,这种情感与俗人何异,读之令人恻然。
明按:此释完全错讲了诗旨。诗详细写道姑“各各能梳略,悉带芙蓉冠。长裙并金色,横帔黄衬单。”此即衣着应有皆有,而且颇具威仪,哪里有一点贫和苦。接着写食,“贫无巡门乞,得谷相共餐。常住无贮积,铛釜当房安。”不仅不愁吃,而且不需预后作备贮。分明是补出一笔:她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社会上不劳而食的寄生虫。诗又言道姑的父母“衣食远求难”,自然是难以向女儿索求,自然是女儿衣食有余而欲求。项书不顾这些明显的事理,仅据一个“贫”字即言道姑贫苦艰难。其实这个“贫”字决应校为“食”字形近之误。“食无”、“无贮积”指同一情况。前层言衣后层言食,并与父母之无衣无食相对比。可证领句意复领层次意的,必应是“食”字。退一步说,即令“贫”字不校,全诗之意也控制了道姑有食有衣。“食无巡门乞”,此有歧解。或:吃的没有就巡门乞。但乞可不饿,也并非常言的贫。或:虽贫而不巡门乞,自有政府配给和檀越设供。沈约《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乃得七十檀越,设供果,食皆精。”至于初唐之时对男女僧道例行优恤政策,“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已是唐史与敦煌学研究者的常识了。贫而不乞讨,犹如俗间骂“和尚没儿孝子多”之语一样,乃讽讥愤慨,属于反语修辞。此首与下面几首共为宗教题材反宗教主题。二五首斥僧徒“生平未必识,独养肥没忽”,〇二六首斥女尼“只求多财富,馀事且随宜。”“不睬生缘痩,唯愿当身肥。”并可证此诗讽女冠而非同情。
出无夫婿见,病困绝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