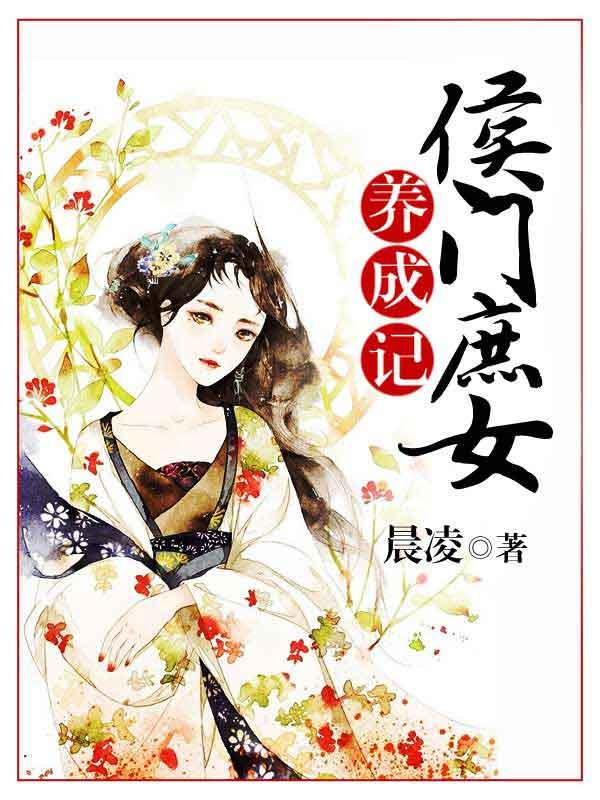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文史述林 >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商兑和补遗(第3页)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商兑和补遗(第3页)
明按:“出”字大有疑,宜详审。如言女道姑出观无夫婿,或父母出家门无女婿,则意味着在观内或家内有丈夫、有女婿,大背事理,复有他碍,此不详析。女儿出家一辈子都无丈夫,因而父母一辈子都见不到女婿,病重将死之时尤为耿耿于怀,甚或死不瞑目,此即诗人所要申言的人伦。故此议“出”为“生”字之形误。《百鸟名》:“独舂鸟……出性为便高树枝。”(852-15)当校为“生性便着高树枝”。《王昭君变文》:“出来掘强”(99。10),当校为“生来掘强”。“绝人看”包括无有女婿照看,亦可证无夫婿非必系于“出”之专意。
乞就生缘活,交即免饥寒。
楚按:生缘,这里指家乡。
明按:生缘,在此实为父母义,父母即儿女生于世上之缘由。?二五首“虫蛇能报恩,人子何由出?”即问生缘为何人。笔者已有《“生缘”试释》文,此不详言。项书言女冠“渴望还乡与亲人相濡以沫”,又说反了句意。僧道不致拜父母,将子女对父母生养死葬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在唐代初期已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政界、俗世强烈要求,政府也多次申令致拜赡养父母,贞观五年、十五年、龙朔二年,开元二年、二一年,都专有诏令。梵志此诗应即缘此而写,并可作为诗人生活于初唐的一个佐证。正因女冠唯求自身肥,所以诗人代天下父母心而乞她们顾济父母,非女冠有到父母身边之愿。如此,则“就”宇于句不安顺,“请求你们到父母处生活”,实质何在?未明言。故疑当作“乞救父母活”,不仅意明,而且合情合理。
《道人头兀雷》(〇二五)
每曰赴斋家,即礼七拜佛。
楚按:理七,指为死者修累七斋追荐亡魂时所作法事。
明按:据此知将该句诗的节奏作:即“同理七,拜佛”。这与本诗及他诗句顿作“xx,xxx”者异,此为一碍。僧人赴斋家作法事实有种种内容,不宜偏狭于礼七一种,此为二碍。今议“礼七”二字误乙,句当为“即礼,拜七佛”,七佛即佛教至于释迦牟尼的七代佛祖。
《寺内数个尼》(〇二六)
莫看他破戒,身自牢住持。
楚按:此处指坚持佛法戒律。《全唐文》九二?知宗《盘山上方道宗大师遗行碑》:“一上云岭,两更岁华,偶因樵采之夫,始见住持之迹。”
明按:既云其“破戒”,又怎会颂其坚持佛法戒律?后文“佛殿元不识,损坏法家衣”;“今身损却宝,来生更若为”,可证数个尼之破戒为实。实则“住持”之义仅是停留、不断,只有言“住持佛法”“住持三宝”之类时,才合成坚守佛法、三宝之意。“身自牢住持”,住持者为“身”,即数个尼自己,指身份地位。句即说她们“诠择补纲维”的升迁全不因破戒而受影响。这只能是揭露。所引知宗文之“住持”实指居住之处,与坚持佛法本无涉(参本文前面第八首“负特”辨误)。该句言,道宗云游山中,形迹不定,问道者难能问津,只有询问打柴之人,偶或可找到他以前的住处。
一一依佛教,五事总合知。
楚按:佛教,此处指佛的教导。五事,指五戒。
明按:此释正是上条误释“住持”的原因。依佛教,应是指投佛教,即当尼姑。“一一”指数个尼,非指佛之条条教导。诗既斥其破戒,就不当颂其坚持五戒。《校辑》于此句作“此事总合知”,注言“乙二本作‘万事’”。应据乙二本定校。句实言她们个个投投了佛教,衣食住行种种事情都合宜了。意思仍在讥讽。
今身损却宝,来生更若为?
楚按:宝,指人身。
明按:她们既都“只求多财富”,“唯愿当身肥”,而且是“富者相过重,贫者往还稀”,分明不是清苦修行,怎么反会损却身体呢?殊为乖理。此“宝”字实应指佛、法、僧三宝,正承应“破戒”,“余事且随宜”之句。如果有碍健康,怎会问到来生的果报?
《佐史非台补》(〇二八)
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不虑弃家门,苟偷且求养。
楚按:出身:入仕途径。《旧唐书。职官志》:“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佐史”即属流外。……可知佐史等“不是好出身”也。又:按佐史身为胥吏,自身可免徭役,家人并无免役特权,故“丁儿”须设计以避征防。
明按:所释含混。“出身入仕者”之“出身”乃专有名词,略等于“规定的资格”。从流外入仕,即从规定的资格之外入仕,亦即无资格,无出身。并非是“不是好出身”。“出身”就字面讲,言从原来的身份转为新的身份,一词可二指。所谓秀才、明经等身份,即指新的状况言,项书另例《朝野佥载》之“令士出身”即指原来的身份是令士。今日所言出身,也是就原来的状况言。诗中是就新情况言,是说丁儿,非言佐史,言丁儿为避征防而逃至异乡这并不是什么好状况。而丁儿是诗中与佐史对立的另一人物,绝对不是佐史的什么家人。“未是好出身”是作者的客观的评说,表示了诗人的同情。项楚同志以为“未是”句指佐史,丁儿是佐史家人必误。“不虑弃家门”两句应是佐史对丁儿的恶骂诬蔑,说他们只求自己温饱而不顾家庭,“且求养”应是“自求养”之误。项书言:“求养:谓要求充当侍养老亲之‘侍丁’,以便不离家门,免赴征防。”这有六碍。诗明言“不虑弃家门”,即实际是弃家门,怎能讲成“不离家门”?此一碍。“且求养”的宾语未明言,何得凭空讲成“养老亲”?此二碍。讲成养老亲又似觉不妥,又再凭空补意为作养别人老亲的“外取,白丁”,外取白丁又怎能不离家门,此三碍。全诗二二句,除首两句外,从“每日求行案”起共十六句都是揭露佐史捉拿逃户,威胁索贿,用四句诗写为家人设计避征防,岂不是游离的拙下情节?此为四碍。佐史家人当侍丁以避征防是梦寐以求的,何又言“苟偷”之不得意?此五碍。无论当侍儿或外求白丁,都是法律允许的,作者写此欲褒或欲贬,实不可知。如把丁儿视为避征防的外乡的丁儿,则一切皆通,而且全篇情节统一,中心突出,主题明确。
每日求行案,寻常恐进杖。
明按:“进杖”,项书及诸家均避而不校不注。此议为“荆杖”之误,句言用荆杖吓人。参见下首“倂檑出时难”条校议。
前人心里怯,干唤愧曹长。
明按:项书仅言“前人”为“对方”义,避言究为何人,也不知他因何罪被捉而判罪。官吏对他是当捉当判而不当受赂,还是不当捉更不当索赂?此“曹长”与前人“佐史”是同一人抑或另一人?都未有交代,作者必不会将叙事诗写得如此拙劣,只能是论者未能读懂。《校辑》把“前人”句以前作一首,此则另析为一首,完全正确。前首揭露地方官吏捕捉逃户,此首揭露官员索赂。据唐李肇《国史补》及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唐代尚书丞郎和郎中相呼为“曹长”。诗之“曹长”是否与此同,尚存疑。
《当乡何物贵》(〇三〇)
处分须平等,倂檑出时难。
楚按:倂檑:颇难索解。疑为出错,失误之义。《变文集。降魔变文》:“者回忽若得强,打破承前倂”。疑即是“倂檑”……意谓此次倘若得胜则可洗雪以前输失之耻。梵志诗则谓“五里官”倘若处分赋役不平等,则难免获罪被罚。
明按:对变文所猜之句意,皆在读者意料之中,难的是对原文词语获得合理解释,且“打破承前之误”之句并不成义。今另提刍议。变文有关文句为“者回忽若得强,打破承前倂清。不忿欺屈,忽然化出毒龙。口吐烟云,昏天翳日……”(386页2行)“倂”乃“并”字误加人旁。那个怪字下面即“雪”字,或为讹体,但似不无原因:草头当为雨头之讹,水旁是因“雨”而重出,雪字的篆体本作“”,中间部分笔画相连,遂与下部一样。这段文句实应标点为:“者回忽若得强打破,并雪承前不忿欺屈。忽然化出毒龙,口吐……”“得强打破”,即得胜打败舍利弗。破、败同义,如《墨子。非儒》:“齐、吴破之难,伏尸以言术数。”《论衡。诘术》:“武王终以破纣。”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捐传业之庆怍,招破败之重灾。”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昔岁军在汉中,东西悬隔,合肥遗守,不满五千,权亲以数万之众,破败奔波,今乃欲当御雷霆,难以翼矣。”“承前”义即从前,“并雪承前不忿欺屈”,并且洗雪了以前心中不平和所受的欺侮委屈。诗句之“倂檑’先就字形应校为“并榈”,繁体“榈”与“檑”在书写潦草者易误。但棕榈有叶无枝,皮可搓绳,别无可用,与句无涉,故应就文意进而定校为“荆杖”。官吏美化自己,说难以出荆杖打人。“荆”字误为“倂”,“杖”字欲误为“榈”而实误成“檑”。这是敦煌抄本特有的辗转相误,一误再误的独特校勘现象,版印书籍无有。
《村头语户主》(零三一)
村头语户主,乡头无处得。在县用钱多,从吾相便贷。我命自贫穷,独办不可得。合村看我面,此度必须得。候衙空手去,定是搦你勒。
楚按:唐代乡头,名义虽为乡官。实为色役之一种。充任者有苦有乐,上首《当乡何物贵》写乡头“乐”的一面,此首则写乡头“苦”的一面,合而观之,唐代乡头之甘苦可知矣。《唐律疏议》十三:“诸部内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答四十,一分答一等。……”观乎此,即知此“搦你勒”之含义矣。
明按:项说仅言“乡头”,未虑其与村头,户主三者的关系。据诗应是乡头向村头说自己无处得钱物,而实是向村头勒索,于是村头又向各户主实告其难,仰求众户出资以供乡头鱼肉。如此乡头何苦之有?此诗与上首实为殊道同归的揭露之作,只是换用题材,并用村头作转述见证而已。诗以村头为最后一环而上及乡头和县上官员,实为一丘之貉,环环相扣,盘剥群众。主题深刻,写法高妙,唐诗中再无此类好诗,项书所言误甚。
《人生一代间》之一(〇三二)
王役逼驱驱,走多换行少。他家马上坐,我身步擎草。
楚按:“走多”谓步行,指贫;“行少”谓骑马,指富。此句言自己今生之贫可换来生之富。乙二本“走多缘行少”亦通,谓今生之穷是由于前生之富。又:此首所表现者,为贫富循环之观念,此亦佛家之常谈。
明按:此解殊为牵强。诗言“王役逼驱驱”,又以“我”步擎草同“他”安坐马上对比,坐马者或为押运的官吏,或为行贿而免役的富人。“走多换行少”只可解为跑多行少,以步赶马,怎得不跑?况且据蒋绍愚《〈王梵志诗校辑>商榷》言:“原卷换字边上旁注缓字,说明抄手先写借字,后又写本字”。(《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5期)戴密微《诗集》即作“缓”。乙二本之“缘”分明为形误,但由于说者所谓贫富循环观念先入之见,遂受蔽而以为亦通,如果承认其通,也只能是跑多因为行少这种循环论证之意,绝不能表述“今生之贫是由于前生之富”。诗之结句:“种得果报缘,不得自烦恼”这本是无可奈何的自嘲语,论者竟据而言其表现贫穷循环了。这也是将精华误为糟粕之例。
《愚人痴涳涳》之一(〇三四)
愚人痴控控,锥剌不转动。身着好衣裳,有钱不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