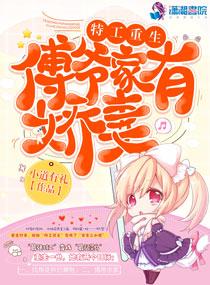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文史述林 > 古代雩祭的文化内涵是生殖崇拜(第1页)
古代雩祭的文化内涵是生殖崇拜(第1页)
我国历史悠久,土地辽阔,学者所记叙的求雨止雨祭仪民俗资料,既丰富而又歧异多变。它们有无一个统一的文化内核,似乎于此做深入考核的极少。本文认为古老的生殖崇拜就是我国古代政府和民间求雨止雨的最原始而又多变异的贯串后世的统一的文化内核。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进行的。求雨,从实质上说是谋求人与气候,因而与农业的调节而达适应,自然更是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儒家学说对求雨是以天人感应说作理论指导的,后世的科学文明或又以此是迷信愚昧来作简单的批判。《文献通考》整个第七十七卷《郊社考十。雩(祷水旱附)》,又全是典章礼仪资料的抄录堆积,完全看不出文化上的根本契机以及由此而来的演变轨迹。如果我们抛开那些繁琐而虚伪的仪礼形式,扣紧远古文化的萌机和核心,就可以看出,几千年来的求雨和止雨之祭,都是在起初生殖崇拜这个基础因子上作同性的改换和异性的遮掩。
古籍所记较早而详细的求雨,是商汤之祷。《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郁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这一记叙突出的重点是商汤严以责已而诚意感天帝,并没有什么特殊性的仪礼。《论衡。感虚》叙此又有汤“自责以六过(《明雩》中言“五过”),天乃雨”的书传之言。《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事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荣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其中叙仪礼也甚简。
六过之说,或是周人对“余一人有罪”的具体化,是为了显示“万民有罪,在余一人”的帝王忧民自责的圣人之心。这种情况是后世帝王求雨一贯沿承去的,成为求雨的最关紧要的,似乎是核心的一项。然而,从文化的契因来说,它是无根的悬浮物。而真正根源的生殖崇拜已被它冲淡或隐蔽了,但仍然遗存着,这就是求雨之地桑林所提示的信息。高诱对“桑林”设注:“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闻一多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已详证,桑林之社即宋国的高楳,相当于楚国的云梦,本都是向女祖先祈求育子嗣的专门祭地。这分明是把人的生殖同农业的丰收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求雨之祭是生殖崇拜的又一种演绎性表现。商汤向女祖祭祀求雨,已经只剩下了祭主和祭地这种生殖崇拜的物化的形式,已是相当文明的形式。可以想象,在更古远的雨祭时,在初民群众自发的雨祭时,必是更原始的,更粗俗而直观的有**本身的内容。弗雷泽《金枝》中介绍了一些地方祈雨的办法是由妇女或少女夜间赤身在村庄边界洒水,或是人们向妇女身上洒水,或是把女性抛在池中。这些都是由女祖生殖崇拜而转向女性生殖崇拜的泛化。商汤在高楳求雨则还是女祖生殖崇拜的直接物化形式。二者的机制是同向的。
所以说,在商汤祭雨中有一明一暗的两个机制。生殖崇拜文化是基础和核心,已被隐曲;帝王自责是附增的虚假的政治因素,却成为主要的内容,呈现出喧宾夺主局势。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行北!’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却是一个多元性的神话,已有后世的加工组合,但仍保留着求雨和止雨的因子,却共系于天女魃一身。于此便可看出女祖生殖崇拜同女神崇拜的转变纠葛,只是过于简单罢了。而且,其中除水道、通沟渎一节,又成为后世求雨活动所承继的第三项内容。
到了周代,祈雨已有定制,并特称为“雩”。雩祭有两种。一种是天子亲祭的常规定时预祭,所谓“四月龙见而雩”,这是为了预祝风调雨顺。另一种是遇旱而祭。雩祭已固定为女巫的专职之一。
《周礼。春官。司巫》:“若国大旱,则帅而舞雩。”贾公彦疏:“谓帅女巫。”又:“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嘆则舞雩。”其中“祓除衅浴”即三月上已祓水洁身习俗的远渊,据学者们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男女桑林之会和女性洗涤女阴以保证生育的习俗,仍是生殖崇拜的遗风。让她们来求雨,正是适得其选的。
《周礼。地官。舞氏》:“教皇舞,帅而舞旱嘆之事。”所谓皇舞,即以雌凰五采羽毛饰舞。《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从这些记载来看,周代求雨活动内容的增减转化要端有三。一,有舞有乐,这是增加的仪礼性内容,它的理论根据是以娱神灵。实际上是为了渲染张扬求雨之事。扩大宣传影响,表示统治者庄重其事。同时,这也是再度遮盖生殖崇拜后的填补。二,设了专职人员,即女巫,是使原始的正常性质的生殖文化转向歧形的宗教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是隐蔽那生殖崇拜的蕴含。而用女巫,却仍遗留着它的原本面目的局部。前引《公羊传》何休注“童男女各八人”一节的机制与此相似,又有新的含蕴。童女未有生育之事,即有正常而充盛的生殖原力,比起女巫来说,在保存生殖崇拜这一点上可以说又是强化。童男则是相及的同性补充而合谐。三,“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说祭祀山川天地时,同时雩祀各地生前有功于民的贤能人士,求其保佑降雨。这应是对天子自罪的巧妙置换,虽然在具体求雨时帝王或仍有此种罪已之辞。总之,生殖崇拜的本质机制即令隐曲,却又从另一个角度或有所突现,而仪礼性则属于新增繁饰。基本上仍是明宾暗主的结构。
《礼记。檀弓下》:“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按:通假曝字)虺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早。公欲焚巫、虺。”所谓“虺”,是专选面部长相畸性的人所充当的巫,即“面向天,觊天哀而雨之”。这一记载充分表明,为了转移或减少天子在祈雨中责任,或者免去他们要自责的不愉快,才设专职的巫,并要特选面向上的妇人。由此再向前推寻,则那成汤的以六过自责,实在就是对当初单纯的生殖崇拜机制的人为的附饰。也就是说最早的祈雨,必只是生殖崇拜一项机制。或者还可以说是用帝王自责的圣人来取代对女性的拜敬,犹如神话中男神取代女神。只是这种取代在周朝时又逆回了一步。
到了汉代,儒家独尊,董仲舒便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用阴阳相成的哲学观重新制定雩祭仪礼。《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阴;其止雨反是。”其实他是在阴阳学说的旗帜之下,更多而具体地恢复了上古生殖崇拜的内容,这是他的雩祭制度的核心。他同样要作遮掩,因而他又使有关的仪礼内容更为繁多而系统。下面即对《春秋繁露。求雨》中的内容因子摘引而作分析。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毋伐名木,毋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处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元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辨口利辞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青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青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乡,其间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诸里〔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膊。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里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之里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闻鼓声,皆烧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
上述设计,全是纯形式性的仪礼内容,即是以五行对应的东方苍龙来寓雨水之象。而蛇、虾蟆也是水栖生物。值得注意的是,完全删去了帝王责已一项,又强调地方性的县、邑、里社和家庭的各自求祭,后者正是前者的取代。总之,生殖崇拜在这些事项上全无关系。夏、秋、冬的求雨,这种情况是一致的,不再赘引。
夏求雨的新的活动内容有:“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毋举土功。更大浚井。暴釜于坛、臼杵于术七日。……令县邑一徙市于邑南门之外五日,禁男子行无得入市。”祀灶,是因为厨事举火属阳,祀而安之,以免阳虐更甚。土功会发泄地之阴气,故禁止。晒釜就是对厨火阳气的惩罚。有趣的是董仲舒把灶神与炊釜巧妙地分开,安抚和惩处软硬兼施。徙市即把集市贸易迁改在小巷中。这本是上古帝王诸侯丧祭的哀礼,董仲舒把它引入祭雨,又规定男子不得入市,是抑阳纵阴的取意。颇为奇怪的是“杵臼于术”一节,未见有人作释。它的意思当是把一套杵臼放在街上暴晒。杵臼代表男阴和女阴,也就是**寓象。
秋旱求雨仪礼中新异的是“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无妻曰鳏,这是泛义。鳏者阳亢而求阴心切,也是以生殖崇拜为底蕴的。
冬旱求祭甚简,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求雨》篇末,董仲舒还有一层重要的补充性说明:“四时皆以庚子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所谓夫妇偶处,即**的文雅说法。所谓“庚子日”,并非五行说的什么含义,实际上是谐音“耕子”。古代性文化中趣谐之说,把女阴喻为水田,还有“三分水田”或“三角田”的形象之言。因之便又有“牛耕田”以隐言**之语。《金瓶梅》中叙薛姑子给吴月娘、潘金莲求子药,嘱咐在壬子日行房事。“壬子”实际是谐音“认子”的神秘说法,即女阴认胎而成子。这与“庚子日”之说曲折一致。可见董仲舒于此暗中补充之意有二。一是求雨的根本机制是男女的**,所以春夏秋冬祭雨其他仪礼尽管有种种不同,此一节却是共同而不可缺的。所谓“家人祠户”主要是指此而言。另一层是如果求雨无验,原因可用未作到“皆偶处”来作遁辞。
《春秋繁露》卷七十五是《止雨》,仪礼性内容简单得多。比如:“雨太多,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其中属于生殖崇拜的一项是:“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这就是以为久雨不睛是因为**亢进而宜节欲。**的亢进又是特从女方为转机,所以要让官员的妻子离开以调节。再对比求雨,正是以为由于**饥饿,也以女方为基准,所以调节的办法是令吏民夫妇皆偶处以遂**。《后汉书。礼仪中》:“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注于此又引董仲舒奏江都王求雨之方,其中有这样的话:“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这“妻各往视其夫”与“夫妇皆偶处”相一致,而与“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相反。却都统一于认为久旱和久雨是可以用**的促或抑来调整。这是最典型,最明显,而又充满信心的女性生殖拜崇。《金枝》所辑世界其他地区求雨的办法虽也多有属于生殖崇拜机制的,但要间接隐蔽得多,已如本文前面所述,只在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上才有类似的直接情况。例如中美洲的帕帕尔人在播种前四天,夫妻一律分房居住,“目的是要保证在下种的前夜,他们能够充分的纵性恣欲。甚至有人被指定在第一批种子下土的时间,同时进行性行为。”如果没有做到,播种即属非法。爪哇一些地方,在稻子孕穗开花结实的季节,农民总要带着妻子到地头进行**(分别见中译本207、208页)。弗雷泽说,这是未开化的种族仍然有意识地用两**媾来促进大地生产。我国汉代的生产和精神文明已达相当高的阶段,董仲舒仍然以生殖崇拜来议定求雨和止雨祭仪,这充分反映出中国远古求雨和止雨的最根本的文化机制就是女性生殖崇拜,充分反映董仲舒对此的深刻理解和诚信,以至于他要订为仪礼而欲恢复。清褚人获《坚瓠集》种芝麻”条:“谚云:‘长老种芝麻,未见得吃。’相传芝麻必夫妇同下种,独种无可得之理。长老,无妻者也。犹忆唐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只不归。’”这“必夫妇同下种”已是演化后的文明遮掩说法,向前推源也必是播种期间伴有**的促进。(该诗即《全唐诗》葛鸦儿《怀良人》,字略有不同)
汉代是儒学独盛的时代,董仲舒又是负有盛名的大儒,他虽是深知先民生殖崇拜对于求雨的文化机制,但他不能明言。他又执著相信于此的,他还要借此而达求雨之效,以解万民之忧。叔孙通已经制定了一般的日常朝仪,于是董仲舒便特为制定求雨止雨的仪礼,来补这个空白。他既要行生殖崇拜之实,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特为设定了繁文縟节的仪礼内容,又躲躲闪闪的,零零散散地寓含了不少了生殖崇拜的实际内容。格局仍然是喧宾夺主,但其中的主却不是完全闭口,而是尽可能露相表白的。
董仲舒把生殖崇拜的内容也是巧妙的置于正统的阴阳理论的帷幕之下。《春秋繁露。循天下之道》卷中说:“君子法乎其所贵。天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谓阴阳。”董仲舒所拟的聚蛇、置蛤蟆、闭南门、开北门,以及旗幡、服色等设计,都统在阴阳学说之内,却也同五行说结合起来。他的最明显而单纯的阴阳即男女的调节说法是:“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乐。凡止雨之大礼,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如果仅就抽像的抑阳纵阴以求雨和相反的止雨来说,这是达意的表述,但同时要兼寓**的合谐却是巧难藏于拙的。因为久旱是以女性的饥饿为喻,就要夫妇偶处而不当男子藏匿,这正是暴露了要用其他的文明理论既遮掩而又传示生殖崇拜是难以两全的。
但是,董仲舒所欲恢复的生殖崇拜,毕竟已失去它当初适宜的原始文化土壤,只成为一种回光返照,无应的孤响。所拟定的“令民夫妇皆偶处”与平日的不令此事,实在没有什么实际差别,而“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或“妻各往视其夫”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实难做到。更加上这种倡议的实际所指和文化含意,也不是多数人所能深解,因之他的理论或设计效果必然为人怀疑。所以这一套仪礼在汉代及其以后,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并无什么影响。后世的请雨、止雨仅是仪礼一项,而且还要简化得多(当然在某些子项上,如供品、拜礼,又如理冤狱、赈恤穷乏等方面,也有趋繁或新增的),至于性崇拜各端则都未被采用。仅是梁武帝大同五年请雨有行七事之制:一、理冤狱及失职者;二、赈寡鳏孤独;三、省徭轻赋;四、举进贤良;五、黜退贪邪;六、命会男女,恤怨旷;七、彻膳羞,施乐悬而不作。这七事在总体上仍是帝王责已改过的政治附会,但使旷男怨女会而乐男女之事,却是生殖崇拜的折射。隋代孟夏后大旱祈雨也有行此七事之记。向后,在政府的雨祭中连这种折射的影子也不见了。
然而在民间非正式的一些求雨和止雨的趣味习俗中,古远的生殖崇拜的影子却往往可以见到。
元代民间有叫“扫睛妇”的剪纸,明清相承。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雨久,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扫晴娘》:“吴俗,久雨后,闺阁中有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帚,悬檐下以祈晴,谓之扫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扫晴妇》诗:‘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其形可想见也。俊民泽州人,而咏如此,可见北省亦有此俗人,不独江南为然也。”清人孙木橒《馀墨偶谈》、郝懿行《证俗文》也都有类似的记述,可见它引人兴味。扫晴娘,即寓含着雨或旱的主动性在女性,也就渊源于原始文化女性生殖力崇拜。
陕甘有这样的民俗谚语:“男绊阴,女绊晴,大姑娘趺跤,太阳红彤彤。”绊倒,指久雨时行走滑倒。它的浅层机制是,男性滑倒意味着阳气仍弱,故续雨;女性滑倒寓示着阴气受挫,故转晴。大姑娘未婚,滑倒即盛阴大挫,故寓红曰临空。而深层文化内涵仍是由单纯的女性生殖崇拜复合了男性生殖崇拜。
陕甘旧时还有另一习俗。久雨时,人或将捶洗衣服的棒槌立在水洼之中,若一立即稳,就意味着速晴或将晴;若离手即倒,便意味着雨将持续。这棒捶立于水洼,分明是男阴女阴器及**的象征,与董仲舒所议“杵臼于术”乃同一类型。棒捶倒即**不谐于男,故不利于生产的气候也不能转为谐调,而女性则是充盛永恒的。女性生殖崇拜的原始比较明显,只是在形式上突出了男性的易于寓象。
又,周作人《谈虎集》中《再求雨》一文写于1927年7月,其中说:“六月三十日,《世界日报》载长辛店通讯:‘昨天长辛店绅商等便联合各界,求雨三天。求雨的形式,是用寡妇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并用大轿抬了龙王游行。用人扮成王八两个,各商家用水射击他。鼓乐喧天,很是热闹。”’
周作人对这种求雨方法有解释,也是不自信而求解。“水淋甲鱼,大约是古时蛇医的遗意,因为他是水族,多少与龙王敖广有点瓜葛,可以叫他传达一声。那个共计四打的寡妇童男
童女呢?我想这是代表‘旱’的罢?经书上说过,‘若大旱之望云霓’,或者用那一大批人就是表示出这个意思来的?希江绍原先生于暑假中分出一部分工夫来研究一下求雨与性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有趣的结果。”
笔者未读到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的有关论著,但以为周作人用性来解释求雨中的寡妇和童男女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童男童女,笔者前文已有说明。至于用寡妇,便和董仲舒议用鳏男是殊道同归,相反相成的。寡妇久无**,所谓性饥饿之甚者,而所欲的男性精液,古典文学习惯以雨露喻说。所以周作人以“若大旱之望云霓”即男女**事作释。应当补说的一层是,董仲舒议言由政府指派鳏男求雨,其在汉代是可行。若到文明的、也总算民主的近代,堂堂男子恐难从命,而软弱寡妇,生活无着的,给以金钱,是可以“请”出为民服务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求雨、止雨,最原始的文化机制是女性生殖崇拜,后世虽然增饰了众多的仪礼,理论或迷信的支持,但生殖崇拜仍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存在着。要用理论或规定的仪礼完全消除它不可能,要用其他的办法再恢复它也难以做到,它只按照自身的规律,既伴随着文明的普及和提高,缓慢地退隐而淡化,又往往遗留下沉淀或痕迹。所以,应当说,古代的求雨、止雨祭礼的发展演变,就是生殖崇拜被掩饰或取代的过程。也就是说,求雨、止雨在起初完全不是基于迷信或宗教原因,生殖崇拜在当初是人类自认为科学认识。后世的求雨、止雨繁增了政治、仪礼、宗教、迷信因素,却也是以原本生殖崇拜为核心而作同向或异向的演变。
对古代求雨作细致深刻研究批判的首推《论衡》。王充认为旱涝是自然现象,与政治无必然联系,而求雨只是一种仪礼或民俗,不是相对应的治水的生产实践,不会有效果。可以说,从唯物主义哲学和历史总结方面,来揭露批判雨祭中的政治欺骗和愚昧迷信,王充是出色地完成了,达到当时甚至后世的思想高峰。
他认为求雨中唯一合理而有益的机制是基于古代仪礼文化大背景的人们的补偿报应心理。即表示对灾害的恐惧、自我谴责、预酬谢天之意。这一认识不能说错,但并不准确深刻。因为他未注意到雨祭中各种机制的变异关系和核心是生殖崇拜,它又是感应文化心理的始源。
《顺鼓》:“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倶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董仲舒设议止雨祭女娲,分明是女祖生殖崇拜因子的恢复。王充不知此文化内涵,他另作回答:“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以补苍天,断蹩足以立四极。’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倘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以为女娲是有神力的公正之阴,便请她帮助君主的阳气,来战胜邪阴。这分明是受了董仲舒祭雨设议中的所谓阴阳学说的虚设圈套。
王充对雨祭的论述,自己是很满意而当仁不让的。《明雩》:“推《春秋》之义,求雩祭之说,实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殁,仲舒已死,世之论者,孰当复问?”显然以孔子、仲舒自比。在科学的批判上,王充是超过他们的,但在生殖崇拜文化内涵的认知上,他却是差逊董仲舒一筹。
求雨民俗机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