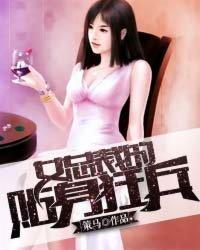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文史述林 > 双恩记变文补校(第2页)
双恩记变文补校(第2页)
1089-3道途辛苦睡深更,善友沉然梦寐成。上士保持虽意在,恶人计较已心生。酌量地里应难趁,顾望天河必未明。取二竹枝签双眼,偷珠连夜发先行。
明按:项先生设注:“趁:追赶。”这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地里应难趁”呢?“地里”指怎样的“地里”呢?都是没有所指的。其实“地里”不是说逃到怎样的地方,才难被人追赶上,而是说乘现在夜里偷珠,是难以被追赶上的。“地里”是“黑地”的误倒,指黑夜。黑夜应难趁:即乘“辛苦睡深更,善友沉然梦寐成”的夜里此时剌瞎他的眼睛而逃跑。“顾望天河必未明”,“偷珠连夜发先行”,都是反复说“酌量黑地应难趁”。
1089-10如是叫换求嘱,亦无人应,遂感树神,故下经云:如是高唱,声动神祇,经久不应。尔时树神即发声言:“汝弟恶友是汝恶贼,剌汝两目。持珠而去,汝今唤恶友何为?”明按:“声动神祇,经久不应”,这样的标点,前后意思却是矛盾的。既然已经“声动神祇”,却怎么又是“经久不应”呢?原来标点应当是:“如是高唱,声动神祇;经久不应,尔时树神即发声言”。因为“如是叫换求嘱,亦无人应,遂感树神”,这是变文的叙述广故下经云:如是高唱,声动神祇,经久不应。尔时树神即发声言”,这是引经文照应。二者是同一意思。即“如是叫换求嘱,亦无人应”与“如是高唱,经久不应”;“遂感树神”与“声动神祇”“尔时树神即发声言”,各是一组照应话句。
1089。14不在高声唱叫频,更深空使动龙神。
明按:“在”是“再”的别写。这里只说到“树神”,而并没有说到什么“龙神”。而树神是被善友的喊声感动了的,对树神言,喊声又不是“空使”了。可见,“龙”字错误,应是“精”字之误。“更深空使动精神”的意思是:夜静更深之时,你再高声呼喊,也是无人听到而白费精力。这与“不再高声唱叫频”是相同意思的复说。
1089-15偷珠将去非珠愿,损汝眼伤是汝亲。
“非珠愿”不成意思,必是“非仇怨”的致误。句言:把珍珠偷跑的,并不是与你有仇怨的外人。“非仇怨”与“是汝亲”对言。下文即说“何怨仇,何骨肉”的对比,充分可怔笔者的校议。“仇”欲音误为“球”,而实际上形误为“珠”。
16何怨仇,何骨肉,合面草头血流漉。
明按:项先生设注:“草头:草里。”但对难知意思的“合面”没有解释。如果“面”指“脸”,则又显然不能是“合脸草头血流漉”这样的措句。“面”应是“眠”的音误字。全句是说:你与恶友,到底是有什么怨仇呢,还是有什么骨肉关系呢:你们二人原来是一同眠在草上的,为什么现在他不见了,而你的眼睛被剌,血流草里呢?
12将为慈悲真我弟,谁知怀此毒身心。和身合面懒能回,石作心肝见也摧。
明按:“将为慈悲真我弟,谁知怀此毒身心”,可证笔者上条对“何怨仇,何骨肉”的解释。
“和身合面”不成意思,应是“何目何面”之误。不是说“懒”于回去,而应是说“难”于回去。也就是没有脸面回去。如果回去,必然要讲明是弟弟把他眼睛剌瞎而偷去珠宝,就家臭外扬了。“石作心肝见也摧”,可证“何目何面”之校。
1093-14向我垂情非世愿,与他为子是天差。
明按:“世”是“他”之误。前文言:“既遭父母相嫌虐,转转思量生恶毒。”本例句则承应而说:想叫父母对我垂情而改变态度,那不合他们的愿望,是不可能的;而我给他们当儿子,那是天意的差遣,我自己现在是不愿意的。
1097-1如是啼哭,伴行数日,到利师跋王国界内。
明按:善友是孤独一人,并没有谁做伴。“伴”是“狂”字成误。“狂行”就是乱走。最早说成“猖狂”。《庄子。山木》:“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成玄英注:“猖狂,无心。妄行,混迹。”无心,即没有目标,不遵道路。混迹,即到处乱走,信步而行。又如《在肴》:“鸿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云将曰:‘朕也自以为猖狂,而民随予所往。’”《庚桑楚》:“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三例“猖狂”均与游、行、往等联系,正说明词义只说具体的行走,不是言与品德相联系的行为,都是说原始社会初民的自由之况。《淮南子。俶真训》同述此义:“当此之时,万民獐狂,不知西东。含哺而游,鼓腹而熙。”可知“猖狂”已有异写词形为“獐狂”。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王率群臣遁去,昼夜弛走,三日三夜,达于秦徐杭山。胸中优愁,行步猖狂。”逃至陌生之地,四顾茫茫,只能是听天由命,信步而逃了。
在魏晋时期的汉译佛经中,可以看到“狂走”即是说乱走。《杂阿含经》卷四七:“猫狸迷闷,东西狂走。”《杂宝藏经》卷六:“遂复前进,被打狂走。值他捕雁,惊怖偉惶,触他罗网。”这个“狂走”,扰是乱走。“狂”仍不同于发狂的“狂”。唐代的书证,又如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书》:“(扬)雄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之猖狂咨睢,肆意有所作。”也就是写文章如行云流水,并无定局死套,“肆意”正提示了此“猖狂”为信笔由意之义。
在《敦煌变文集》中,累见“猖狂”此义,或异写为“獐狂”、“麖狂”。《伍子胥变文》:“女子拍纱于水,举头忽见一人,行步獐狂,精神恍惚。”这是写子胥逃国,前文巳言他不谙道路,“信业随缘,至于颖水。”《张义潮变文》:“承珍忽于旷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处分左右领至马前,登时盘诘。”此人是唐朝使者,他答言:“汉朝使命,北入回鹊充册使立。得至此间,不是恶人。”“行至雪山南畔,被叛乱回鹘劫夺国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信脚而走”正是词义。《张义潮变文》:“蕃贼麖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行便追。”这是说敌人四面乱逃。《伍子胥变文》:“枪沾汗血,箭下猖狂。”写箭射得敌人乱逃。
《秋胡变文》:“学问完了,辞先生出山,便即不归,却投魏国,意欲觅官。披发倡伴,佯痴放呆,上表奏进陈王,誓不见仕。”其中“倡伴”也是“猖狂”之误,指乱走。与“佯痴放呆”承应。这种写法与《伍子胥变文》一致:“子胥问船人曰:‘吴国如何投得?’船人曰:‘子至吴国,入于都市,泥涂其面,披发獐狂,东西驰走,大哭三声。’”而所谓“东西驰走”即东西南北,四向乱走。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把“披发倡伴”校正为“披发倡伴(佯)”。并设注:“原文‘伴’《变文集》校作‘狂’,字形稍远,当作‘佯’。倡佯,散诞闲游貌。”其实《变文集》以文意校作“狂”是完全正确的,在古代文学中,“披发”就是不拘礼法而狂乱的标志。散诞闲游与佯痴放呆不能承应。
上述失校之处,在《敦煌变文校注》中相同。
《敦煌变文选注》中的《双恩记》只是卷七及卷十一两部分,未选卷三部分。《敦煌变文校注》中的卷三部分,也有一些失校之处。本文也试申校勘及注释讨论。也是先标示文句的页数行数。“校注”之类,指的是《敦煌变文校注》原有的“校注”及编号。
924-10涌身虚空,高七方罗树,身上出水,身下出火。东涌西没,西涌东没。
明按:“身上出水”句,核查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14页,影印原卷第19行,原作“身上出木”。但研究者对“身上出木”或“身上出水”的意思,都避难而不解释。今议,“身上”就指全身,而不是仅指身体的上部,因为没有仅指身体下部的“身下”一词。所以,“身上出木”的“出木”与“身下出火”的“身下”,都是衍文。原文应只是“身上出火”一句。“出火”指闪光。此承应上句:“世尊以一道光照其阿罗。光才照身,寻便自在。涌身虚空……”因“身上出火”而误衍“出水”,又被误成“出木”。又,“涌身虚空”“东涌西没,西涌东没”中都当校为“踊”:跳跃。
又,“七方罗树”应是“七多罗树”之误。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七多罗树:(植物)多罗树者,多罗叶之树,高木也,故譬物之高,辄曰七多罗树,言比多罗树高七倍也。《法华经药王品》曰:‘坐七宝之塔,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智度论》二四:‘千阿罗汉,闻是语已,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又,“多罗”的第二义:“树名。译曰岸树、高竦树。玄应《音义》二四:‘多罗,按《西域记》云:其树形如棕榈。极高者七八十尺。果熟则赤。如大石榴。人多食之。东印度界,其树最多。’”
924-13坚请阿难升座说法。未说间,大众有疑,忽然间道:“如是我闻”,大众方知是阿难。
校注:原卷“间”字,多家录作“闻”,臆改不足据。
明按:但核查原卷第26行,当判为“闻”字,与其他处“闻”字笔形一致。即其中的“耳”字,左下角是竖笔与横笔的相交关系。而“间”字中的似“日”字,左下角是竖笔与横笔的两端相切关系,即都不出头,分别十分明显。“忽然闻”是大众忽然闻到阿难的话,意思显赫。
14若遇西天獅子脂,不销一滴皆成水。
校注:不销,犹“不消”,不需要也。
明按:“一滴”就指极少量。如果是说不需要一滴,那么是需要多少呢?对于“滴”,是不能再分成半滴、三分之一滴等等更少的量。也就没有半滴、三分之一滴等说法。“不”是“只”之误。前文:“信如獅子乳、皮:乳一滴入于众兽血中,尽变为水。”《华严经》七八:“譬如有人以牛羊等种种诸乳,假使聚积盈于大海,以师子乳一滴投中,悉皆变坏直过无碍。”都是说“一滴”。无须变说成:“不销一滴”(用不上一滴)。《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启言不得说:‘大王照知否:贫道生年有父母……’。”其中“启言”与“不得说”矛盾。明明是说了很多话,怎么是“不得说”呢?《敦煌变文校注》有感于此,校点为:“目连启言:‘不得说大王照知否?……”。但“不得说大王照知否?”中的“不得说”实在是大有隔碍的。应该校正成“目连启言只得说”。即只得把母亲生前种种恶行说明,而这一般是不愿意说的。《金瓶梅》第七回:“你老人家去年买春梅,许我几匹大布,还没与我。到明日不管一次总谢罢了。”其中“不管一次”是“只管一次”之误。即把两次的谢礼一次总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