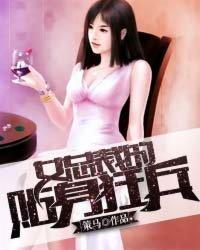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文史述林 > 感谢石汝杰先生的批评与申说(第2页)
感谢石汝杰先生的批评与申说(第2页)
但石先生绝大多数的批评,我以为并不能成立,或往往倒是石先生自己错了。下面逐条申说。
石先生文章一开始说:刘氏对吴语的语音了解甚少。冯梦龙在全书开头处,就对书中语音作出了重要的说明:“凡‘生’字、‘声’字、‘争’字,俱从俗谈叶入江阳韵。此类甚多,不能备载。”(卷1笑)刘氏对此无法理解,称:“冯评所言‘生’字等,……这是对全书说的,本首无此情况。”按,其实,本首里用到的“后生”,就属于这一情况。
我这个注解没有丝毫的错误。因为冯梦龙分明说的是“叶入江阳韵”,即只是对句末的押韵来说的,而本首诗四句的末字是:来、开、笑、来。并没有以“生”字作韵脚。“生”字是在“后生娘子家没要嘻嘻笑”句内。卷八《丢砖头》的韵脚字是:场、声、量、量、肠、张、扬、方、量、肠。这才是冯梦龙说的“声”字“叶入江阳韵”,所以我注解“声”字:苏州读shang,故与“场”、“量”合韵。参见本书卷一《笑》注(一)。”而按石先生之说,则苏州“生”字只有shang—音。但《苏州方言词典》第177页“生”字条音shang,第215页“生春阳”条,“生”字音音sheng。可见我说的正确而石先生说得不全面,有意掩盖了“生”字也音sheng。
石先生文第一部分是用这样的谐音理论批评我的:一般情况下,谐音要求同音,至少在声母、韵母和声讽三个要素中,有两个相同,另外一个比较接近。吴语入声和非入声差别很大,谐音的可能性更小。
按,通假分同音通假与近音通假,谐音也一样,也分同音谐音与近音谐音两种。声、韵、调全同,声、韵全同而调不同都是同音谐音,声、韵相近是近音谐音,声、韵是相近而不是相同,声调的同就没有意义。没有谁作“一般情况”的规定,因为无法区分怎样是或不是一般情况。不仅吴语,凡是有入声的,和非入声差别都很大。石先生为什么不说根本不可能谐音呢?而古诗已经有入声和非入声可以合韵。鲁迅《哀范君三章》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当时自由党主持人何几仲,排挤范爱农,为范爱农所鄙视,所以说白眼看鸡虫。鸡虫,是‘几仲’的谐音,这里是一语双关。”而“虫”与“仲”,难道不是近音谐音吗?《苏州方言词典》附录《苏州地名特殊读法》:“这里收的地名读音都是跟单字音有差异的,纯属老一辈人的读法。”共51个地名。其实都是谐音或写别字。例如北浩街、南浩街,本是北壕街、南壕街。“浩”与“壕”声韵相同,声调不同。又如因果巷本是鹦哥巷。“因”与“鹦”声韵都不同。“果”与“哥”声韵相同,声调不同。《苏州》“鹦哥:鹦鹉。苏州有因果巷,读成鹦哥巷。”《苏州方言词典》摆姆两家头:妯娌两人。摆可能是伯字音变。”“烧麦:烧卖。”而“摆”“卖”没有喉入声尾,“伯”》“麦”有喉入声尾。又如《武汉方言词典》说“鸡杂”谐音“稽查”》“糯米坨”谐音“呵弥陀”。如此例证甚多,不再举。而按石先生的理论,都是不可能谐音的。
石先生文实际都是仅用声母不同、清浊不同、韵母不同、声调不同的某一不同批评而说我解释的谐音是错误的。这又与他说的“有两个相同”就可以谐音矛盾。但是,实质性的仍然是文意。字面能讲通的就必不是谐音,字面不能讲通的就可能是谐音。把文意讲通了就是正确的。石先生否定我的正确的谐音解释,则文意不能讲通,因而石先生避言文意。下面各例||号前面的都是石先生原文,后面的是我的申说。
1。(1)青滴滴个汗衫红主腰,跳板上栏干耍样桥?(卷1骚)刘注:耍样桥:谐音说她是多么“娇”。按,应是和“乔”(漂亮)谐音。||《明清》(按,指石先生主编《明清吴语词典》)501页“乔:好看,漂亮”,也仅是此孤例。但“乔”绝对不可能有此义,所以其他吴语词典都不载此义。
(2)出名虎丘山到弗高,第一等快船到弗是摇。(卷1弗骚)刘注:摇:谐音“妖”。但声调不同。||我的注解是:第一等快船:用足蹬水轮前进的船,不用摇撸。摇:谐音“妖”。石先生回避是否摇撸。我解释的“弗妖”正与题目“弗骚”一致。
生炭上薰金熬坏子银。(卷1熬)刘注:熬坏银:损坏银,谐音“恼坏人”。按熬、恼”不可能谐音。“熬”的意义很明确,就是煎熬。本书用例很多。||但薰银犹如镀银,可以说是浪费,不存在把银煎熬坏。对贫穷、病痛、酷刑说煎熬,对久久等待不能说煎熬。“熬、恼”是近音谐音。今再补言,“熬坏银”是谐音“恼怀人”:因怀念而恼,即恼他不来。
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做子缯竿多少斑。(卷1作难)刘注脱”谐音“拖”。斑,谐音“扳”的推辞义。按,从文意来看,“斑”无法解释为“扳”,释为“悲”更合适些,后者苏州方言同音。||诗前两句是“今日四,明日三,要你来时再有多呵难。”这正是“拖”,也正就是题目的“难”。而“悲”则与题目不承应。从“后者苏州方言同音”的话来看,是说“斑”与“板”在苏州方言不同音,所以不能谐音。但《苏州方言词典》与《明清》所附录的《苏州方言同音字表》中两字都同音同调。
(6)典当内无钱,啰弗说我搭你有。(卷1捉奸)
刘注:无钱:谐音“无见”,无证见。“钱”从母;“见”见母。不能谐音。||无钱与没有奸情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奸情的证见,就不能说有奸情。就是结句的“月亮里提灯空挂明”。“钱”从母;“见”见母。近音谐音。
(7)姐道:“郎呀,隔夜汤团,我听你也是宿水圆。(卷2长情又)刘注:宿水圆:隔夜的团子。双关“宿缘”。但是“水”没有着落,其实和“宿世缘”谐音,这里“水世”同音(因有连读变调)。||是有遗漏,而不是错误。
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卷3久别)刘注:透风:谐音“投逢”,相逢。按,投逢,不成词。||投:投合;遇:逢遇。而“透风”与“见面”无关。
姐儿昨夜嫁得来,情哥郎性急就忒在门前来。(卷3思量)刘注:忒特”的近音代写字。按,忒,动词,转悠。||《明清》594页另解释成:忒:偷偷地转悠。但“忒”无从有这样的词义。而618页“脱:同‘忒’。偷偷地行走;溜。”自我矛盾。又,“转在门前来”的话也不通顺。
你嫌我筛得弗爽利时,要便再滴子厾去。(卷5筛油)刘注:滴:原注:“滴,音‘帝’。”这仅是注音,无关意义。其实是对这一词的方言读音和用法的记录,是很宝贵的资料。因刘氏不懂其价值,以至有此一说。||石先生既然懂得宝贵价值,为什么不能说价值在哪里,而与意义有关的又应另是什么意思?
—铁搭挵出子十七八个夜叉。(卷5骗)刘注:捹:同“蹦”。按,此例里用到了农具“铁搭”(锄头),只能理解为“坌”(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锄一下,不可能把十七八个夜叉都锄在锄上而带出来,只能是在锄开的地方一个接一个蹦出来。
栀子花开心里香,乌龟也要养婆娘。(卷5乌龟)刘注:心里香:谐音“心里想”。按,“栀子花”在这里是起兴,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民歌的兴,情况是比较灵活的。早在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就说“兴有时与正意有关,有时无关,有时有情调上的联系,有时只是从韵脚上引出下文。《诗经》里的起兴情况比较复杂,它有时兼比义……也有些兴句起象征的作用……《诗经》里也有完全‘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的起兴,所谓以声为用。但也不一定只是趁韵而已。例如《秦风。黄鸟》三章的兴句是‘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这和下文‘三良’殉葬的事,意义上不可能有联系,但是棘和瘠音近,桑和丧同音,楚和痛楚之楚又是同字,这三个字仍然能引起忧伤痛苦的联想。”即兴也可以结合谐音。可比较《古艳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是指婚姻与爱情的弃旧图新。但灰色、黑色、棕色的兔子都有孤独失偶的;任何毛色的任何动物都有孤独失偶的,为什么偏说白兔?“白兔”是“百图”的谐音;“茕茕”是“穷穷”的谐音。穷穷百图:穷尽性的,千百次弃旧图新。
又,《闻一多诗经讲义》:“‘兴’的问题。闹了几千年而没有人能解释,感谢抗战,使我们到了大西南,接触了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保存了较古的民歌形式’我们可以用以与《诗经》比较。用民歌与《诗》比较,就可以明白‘兴’是什么了。……闻先生《说鱼》一文谈‘鱼’字在《诗经》中作‘兴’之用法,尤其在《国风》内,只有极少数是做本义用的,多是男女互用以称其对方。不但《诗》如此,即自来古书,宋人笔记,乃至今之民歌,皆然。”“‘兴’就是隐语。……在中国语言中,尤其在民歌中,隐语太多。”
我当初只道你红红绿绿是介件赢钱货,啰得知你滚来滚去到是一个老幺精。(卷6骰子又)刘注:赢钱:谐音“迎前”,指到身前幽会。幺:……谐音“摇”,指分离。按,说的是“骰子”,说赢钱是普通的事。这里显然与“老妖精”(本书中这一词出现两次)谐音,不必另作解释。||诗是说:结识的私情不能像骰子“随人抛掷骨头轻”,即听别人教唆而结束私情。但赢钱与情人无关。骰子无所谓“老妖精”,妖精也与情人无主见无关。骰子是转动不定的,正指情人的摇摆即分离。
要长要短凭郎改,外夫端正里夫村。(卷6海青)刘注:改:谐音“盖”。外幅:面子,谐音“外夫”。刘氏把后半句改为“外夫(幅)端正里夫(幅)村”,原因是他不明白“夫”的意义(衣襟,一般写作“袂”)。||但不能说明郎“改”她的什么。衣服的里子全部都是较次的布料。而里襟与外襟,就是大襟与小襟,却是用同样的布料。里襟即小襟,并不是衣服的里子。
阁来呵,阁来呵。再搿搿,再搿搿。(卷7田鸡)阁,刘氏改为“哥”。按,阁来呵,当是“放在这里”。||例句是模拟田鸡半夜的叫声而赋予**的含义。搿,指双手合抱。即“阁来呵”也应言**。“放在这里”,则不知究竟把什么放在哪里。
姐儿生来身小眼即伶。……你生罗卜到口豁声能。(卷7后庭心)即伶,刘氏改为“机伶”。刘注:豁:吴语音如普通话的“哗”。按,即伶,是常用词,即机灵,灵活。“机伶”,不成词。||《汉语大词典》机伶:机敏伶俐。”引例靳以《凛寒中》:“sp孩子却机伶……。”周立波《金戒指》:“勇敢机伶的张海……。”“机伶鬼:机敏伶俐的人。”引例茅盾《某一天》:“这是个机伶鬼……”而“即伶”字面不成词,应释难而回避。
搿子我汗弗离身,勾子我手弗离颈。(卷8竹夫人)刘注:汗汉”的误字。句谓汉子即丈夫不离身。竹夫人是为纳凉止汗,绝不当言汗不离身。按,竹夫人用来纳凉止汗,有汗才需要用,是很自然的。刘氏的解释站不住脚。||竹夫人是要使人身上的汗离开,即消失,绝不当言汗不离人身,也绝不是把人的汗移到竹夫人上而不离身。使用竹夫人无所谓“勾子我手弗离颈”,因为竹夫人无所谓颈。
汤婆子,你弗许你热绰绰乱搂,要温存。(卷8竹夫人)刘注:热绰绰:“热匝匝”的记音代号。吴语“绰”与“匝”音近。||但并没有说出错在哪里,应另是什么意思。
好像漏湿子个文书失约子我。(卷8睏弗着)刘注:漏湿漏失”之误,即遗漏丢失。其实“漏湿文书”和“失约”谐音“湿”和“失”谐音“文书”与“约”义同),是很典型的谐音现象。||如果是谐音,就如同制谜,其中不应有丨迷底。后文明确说“失”,则不是制谜,前面就无须隐蔽为“湿”。只应是误字。“漏、失”复指,而“漏、湿”不能复指。文书湿了,不能说成漏了。
在前还有青龙上卦,去后只怕白虎缠身。(卷9山人)刘注:“青”谐音“庆龙”谐音“隆”,所以是上等吉卦。“白”代表死丧’“虎”谐音“祸”,所以是凶卦。“青龙”和“白虎”对举,根本不必用谐音来解释。《汉语大词典》说,青龙,古时以为祥瑞之物。常与“白虎”对举,用以表示一对相生相克的事物或概念。白虎,特指迷信传说中的凶神。可见对这些很常见的词语,作者的理解也有问题。||但并没有“青龙卦”与“白虎卦”的卦名。白虎也是虚拟的瑞兽。《瑞应图》:“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苇则见。”《孝经援神契》:“(王者)德至鸟兽,白虎见。”也有把青龙说成凶煞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白虎与青龙”条:“阴毛阙如,谓无毛症。女性患无毛症,民间俗称‘白虎’;男性患无毛症,民间俗称‘青龙’。阴毛同汗毛、胡须一样,由于个体的差异存在着有与无,疏与密的不同。而阴毛的发生受性激素的制约。……但民间有认为‘白虎’或‘青龙’均为不祥之兆,有‘患女克夫’、‘患男克妻’的说法,这是一种荒谬和迷信的认识。”迷信或神秘文化所谓的青龙、白虎的具体内容都是蕴含在谐音中,所以这里也是如此。
褥子上番身无席摸,千条锦被弗如郎。(卷7寂寞)刘注:席摸:“摸”似乎当作“幞”,复指席。按,“席摸”显然就是和“寂寞”谐音的,冯梦龙在标题里已经标明。刘氏还费尽心机曲折作解,实在没有必要。||但冯梦龙在标题下只有“中犯《皂罗袍》”五个字的曲调解释,并没有“席摸”是和“寂寞”谐音的标明。更重要的是“无寂寞”正与诗题即诗意是“寂寞”相反,可见石先生解释错误。
2。(1)思量同你好得场騃。(卷1睃)刘注:騃:苏州话的记音代写字,义为一定。按,騃,就是“呆”,不可能是副词用法。||《苏州方言词典》》呆:1不灵活。2副词,必定。”“呆板:副词,必定。”“呆板数:可以预测到的、一定的、很少变化的。”《简明吴语词典》》“呆板:副词,必定;一定。”騃,音^,与“挨”“埃”“唉”的得声相同。所以被用为声音相近的“呆”字的别写,意思是“一定”。石先生说不可能是副词用法,即是形容词而指傻。但全诗是:“思量同你好得场騃,弗用媒人弗财。丝网捉鱼尽在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与傻完全没有丝毫关系。
姐在房中吃螃蟹,呀,缩缩脚,心肝爱。(卷1睃)刘注:缩缩脚:……吃螃蟹时蟹脚会收缩。按,这里说的是吃螃蟹腿里的肉时,常用吸(“嗍”,和“缩”同音)的方法。下例中“缩”的用法同。好似橄榄上佥皮捨弗得个青肉去,海獅缩缩再亲亲。(卷2姐儿生得又)刘氏改为“唆唆(声调也不同》“缩”是入声,“唆”是平声),误。||但姐吃螃蟹与实际要说的**风马牛不相及。“螃蟹”是“髈、谐”的谐音。髈——大腿——男阴。为了**谐和,叫郎向下缩腿。这与下一首说”再上些”,都是傻女婿故事中新婚夜妻子教傻女婿的内容。
大门阁落里日多介两三遭。(卷1骚又)刘氏不懂“ye”的含义,引了《集韵》和《汉语大词典》,还不敢肯定,说“仅作参考”。其实,《汉语大词典》释为“紧靠着物体躲闪的样子”,基本正确,只是把动词解释为“……的样子”,不妥。||问题是《集韵》的“填”义与“紧靠着物体躲闪的样子”距离较大,所以说“仅作参考”。
二十姐儿睏弗着在踏床上登,一身白肉冷如冰。(卷1熬)刘注:踏床:床前的简易木凳,便于上床和放鞋。按,踏床,是床前的木制平台,高约20公分左右,长度和床一样,作用确实是为了便于上床和放鞋(主要是防湿的功能)。||《苏州方言词典》:“踏脚板:床前面的木板,长与床等,宽二尺左右,四角有矮脚。《上海方言词典》:“踏板:旧式床前放置的一块木板或矮木几。《汉语大词典》:“坐时搁脚的小几。《宋元明清百部小说大词典》:“置于床前搁脚的小凳。《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床前搁脚的小凳。《近代汉语词典》““床前承足的小几,即脚凳。”有矮脚也就是凳。几,有腿而矮,就如凳。可见我的解释无误。那么多的辞书与我的解释相同,石先生为什么不说他们都是错误的呢?又如《武汉》:“踏板:旧式床前供上下床脚踏的板,有腿,像长而宽的短凳。”也以“凳”比较而解释。
咦怕情哥郎去子,喝道“风婆婆,且在艸里登。(卷1引又)刘注:登等”的记音代替字。按登、等”声调不同,意义也无关。登,是典型的吴语词,待(dai)。||仅声调不同也可谐音,例句正是说在草里等待情人。《简明吴方言词典》登:1居住。2呆;停留。《苏州方言词典》登:临时住。《温州方言词典》登:驻。”但不切合诗意。而《崇明方言词典》《丹阳方言词典》《宁波方言词典》《上海方言词典》都没有”等:待”的词义。但姐吃螃蟹与实际要说的**风马牛不相及。“螃蟹”是“髈、谐”的谐音。髈——大腿——男阴。为了**谐和,叫郎向下缩腿。这与下一首说“再上些”,都是傻女婿故事中新婚夜妻子教傻女婿的内容。
汗衫累子鏖糟拚得洗,连底湖胶打弗开。(卷1娘打又)刘氏注:累子鏖糟拚得洗:积累了许多污垢,干脆不洗。按,累,义为“沾(污)”。||《山歌》每一个词都是吴语词,完全没有普通话词语吗?“累”只是吴语,而不是普通话吗?胡明扬文章说:“冯梦龙辑录这些小调民歌用的不纯粹是方言,而是文白夹杂的,也许原本如此,也许写成文字时经过润色修改。”“在词汇方面,即便是《山歌》也使用了大量的北方话,而吴语词汇也不局限于苏州一地。《明清》的《前言》说:“本研究的难点还有一个,就是很难得到纯粹的方言资料。我们见到的文献,语言面貌相当复杂。大多是方言和官话混在一起的。”“《山歌》和传奇中有成段的方言,但是也夹杂通语的用法。”周志锋《大字典论稿》199页:“累:沾;沾上(不洁之物)。”就有此例,因此我是知道的,但不取。因为“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叫郎夜夜来。”积累,即承“夜夜”、“拼”、“连底湖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比“沾(污)”义胜。自然,也可以用吴语词义解释而两可。石先生另文《关于苏州的语言(之一)》中说:此句实际意义是“汗衫沾上了污垢无非一洗(这里“洗”和“死”谐音)。强调姑娘“拼得一死”的决心。但是,“拼得一洗”“无非一洗”则是用力洗去污脏,就是表示要改正错误,则与“连底湖胶打弗开”表示不改正不分开恰好相反。可见解释错误。我的解释“干脆不洗”,就是不改正不分开。
急水滩头下断,而“抹”音。但仍然是近音谐音。而这仅是苏州的读音,在整个吴语区,也可能有更为同音的,词就产生于此,因为“言之有文”而被其他地方吸收。就像“六六大顺”的话,本是“六”与“禄”同音的方言的说法,也通行于“六”与“禄”并不同音的许多地方。所引的“淫筹”也是不确的。因为“筹”是竹或木片,古时用于在厕所擦屁股,叫“厕筹”。《北史?文宣帝》虽以杨愔为宰辅,使进厕筹。”明陶宗仪《辍耕录。厕筹》:“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没有在**后用竹木片拭秽的。
(1)“未曾曾”,书中出现两次,刘氏都认为是错字。如:结识私情未曾曾,外头咦话捉奸情。(卷1捉奸)私情起意未曾曾,咦有闲人搬来我里个听。(卷7钉鬼门)刘氏注为:未曾曾,此三字不成意,当是“未着身”之误。按,从文意来看,都表示尚未(有、实行)。吴语常用类似“未曾不曾”的格式表示否定过去动作(相当于“没有”),“未曾曾”当是由此生发出来的。||不仅吴语,就是普通话也常用“未曾不曾”表示否定过去动作(相当于“没有”),为什么没有生发出“未曾曾”来呢?《明清》630页,未曾曾:形容事情尚未发生。仅此两例。难点是第二个“曾”字。为什么把“未曾”说成“未曾曾”呢?如果“未曾曾”就是“未曾”的意思,则没有“结识私情未曾”“私情起意未曾”这样的说法。否定副词“未曾”应在被否定的动词前面。如果有“未曾曾”的词,就不会仅是这两例。原文并不是“未曾结识私情”“未曾私情起意”的意思。《捉奸》只是说没有奸情。冯梦龙评语:“一云结识私情未着身’外头咦要捉奸情。……弱者奉乡邻,强者骂乡邻,皆私情姐之为也。因制二歌歌之。一云:姐儿有子私情忒忒能……。”分明是“结识私情未着身”,是“私情姐”。
(2)又如“哱喽喽”,摹拟低语声。从本书的两个用例来看,其意义很明显。可是刘氏分别作出不同的解释。如:痴乌龟口里哮喽喽介通陈,只捉家婆来保佑。(卷2保佑)
姐听情哥郎正在床上哱喽喽,忽然鸡叫咦是五更头。(卷2五更头)第一例刘氏的注为:哮喽喽,表示低声自语,别人听不清的象声词。按,这一说法还比较正确。第二例刘注却为:哮喽喽:鼾声。按,第二例中两人正窃窃私语忽然”天就亮了。所以要怨恨钦天监了。||比较正确即不完全正确,只说“摹拟低声语”就是完全正确吗?“正在”是吴语独有的词吗?普通话没有吗?吴语“听”只有介词“跟”的意思,没有动词“听”的意思吗?《挂枝儿》卷七《鸡》(之一):“俏冤家一更里来,二更里耍’三更里睡,四更里猛听得鸡乱啼,挦毛的,你好不知趣。”广东翁源山歌:“鸡子唧唧就天光,细声细气喊醒郎。唔曾同郎拜天地,唔敢留郎到天光。”都是写郎因耍而劳累酣睡,而她则醒,听见鸡叫就遗憾郎不能睡足。可见不是说她与郎窃窃私语。
(3“只有”的用法。《山歌》里,共有12处用到“只有”,大多是普通的用例,如:百样鸟儿百样声,只有青花样箇田鸡叫得忒分明。(卷7田鸡)但是下列3例中的“只有”比较特殊,刘氏都认为是“只因”之误。姐儿嘱咐小风流,只有吃个罗帐里无郎弗好留。(卷1孕又)郎呀,只有吃个硬壳乌龟拘官得我介紧,无钱弗放我自开门。(卷6厘等)只有贪杯着子郎个手,吃郎亲亲啧啧再斟斟。(卷6酒锺)从这些用例来看,刘氏解释为表示原因的“只因”并没有错,但是既然有这么些实例,就应该认定有这样的用法。不能一概斥为错误。||“只有”绝对不可能有“只因”的意思,只能是字误。这应是我的正确处,竟然被批评为错误。“例不十,法不立”。但,即就是有这样的十例,也不能立“只有:只因”的词义,因为“有”绝对不可能有“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