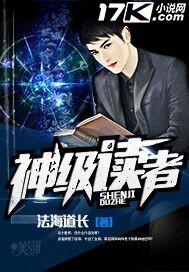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鬼才郭嘉之三国重生txt > 孟德接招(第2页)
孟德接招(第2页)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刘琮率荆州降曹,司马徽也为曹操所得,欲大用,惜不久病死。
光顾襄阳城,要看隆中景;参观三顾堂,必知水镜庄。
水镜庄作为东汉时期著名古文经学家司马徽的隐居地,早已成了古三国旅游线上的一处重要历史遗迹,目前正作为襄樊市实施“旅游强市”的一大不可缺少的法宝,而逐步被卓有成效地开发利用。素来被古今之人誉为“雅士”、“高人”的司马徽,由于学富五车,自甘清贫、不图权贵,善于知人、识人、育人,并且胸襟博大、甘当伯乐、荐贤举能,遂被时人尊称为“水镜”先生,大名鼎鼎的“水镜庄”便由此而来。
了解水镜庄或者到过水镜庄的人,未必就知道玉溪山。其实,水镜庄与玉溪山是母子联体,相依为命的,因为水镜庄就座落于风景俏丽、仙气悠荡的玉溪山一侧。慕名而来的观光者,可能比较难想到,在他还没有涉足水镜庄前,她的母亲——玉溪山已经翅首以盼,正一如既往地张开着她那迷人的胸怀,迎来和送走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景仰人。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说实在的,海拔不过千米的玉溪山在荆楚大地上,只能算作是“土包子”,与鄂西北山区的众多山峦相比较,她既称不上崇山峻岭,也不算是悬崖峭壁,但就因为“水镜”先生在此躬耕修道、授业解惑、培养和举荐了文韬武略、名垂千古的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及庞统等栋梁之才,遂为世人所由衷敬仰。假设司马先生当初不在玉溪山隐居,而是选在了古荆山的其它什么角落生活,届时,“水镜庄”可能照有,而玉溪山则不一定就会有如此越来越大的名气了。是故,先有司马徽,后有水镜庄,再有玉溪山!
历史的确时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玉溪山的来历不过是因为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环山脚流过而得名,古老的乡民们当初并不知道司马徽为避战乱寓荆襄,并要来此长期栖居,而不想他老先生莅临之后,不仅仁爱厚道,与人为善,而且胸怀博大,精心育人,更了不起的是,他大智若愚,韬光养晦,甘当伯乐,力荐大贤,促成卧龙出山,凤雏高飞,德高望重,遂得“水镜”雅名。“玉溪”—“水镜”,多么美妙绝伦的字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溪”与“水”、“玉”与“镜”之间,巧夺天工,相辅相成,存在着天然的异曲同工之处,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思虑,是不是因为司马徽与玉溪山存有前世因缘,或者心灵感应?玉溪山的存在是为司马徽的隐居,司马徽的到来是为玉溪山的召唤,二者血脉相通,不可分离。
外地人大多由司马徽知道了水镜庄,而后才有可能逐步了解玉溪山。本地人正好相反,可能全都知道玉溪山、水镜庄,但未必都很清楚司马徽。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很多时候,本地的人文景观似乎要靠外人来发掘和肯定,到实地调查参观学习,好像是外人的事儿,与自己无关。你观光我收钱,坐收渔利,天经地义,何其快哉!孰不知,风景停落山野,历史飞流时空,司马圆寂尘土,唯有精神永垂不朽。作为有幸经历和铭刻了古三国时期重大人物事件的一片热土,景观仰头可见,早已烂熟于胸,但如果见惯不怪,习以为常,并未吃透和得到多少司马其人其事的思想精髓及其德操精神,也没能进而援古弄今,经世致用,醒励当世,促进发展,岂不可悲可叹!?这似乎正应验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古话。
笔者同世人一样,至为崇敬和钦佩先生司马徽,因为他的确有着不同凡响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想想,一位生活在1700多年前的古人饱学经书,潜心育才,声名远达,但贞操自固,不求显赫,坚守清贫,甘为人梯,辅佐社稷,该是何等的思想境界啊!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虽避乱于荆襄,不求荣达于诸候,不苟同于世俗权贵,但仍然胸怀大局,潜心研读治国理政安民之道,广结天下有识之士,既知人爱才,倾其所有,诲人不倦,又将贤能徒弟扶上马、送一程,力求终成大器。他对诸葛亮的教育、培养更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堪称杰出典范且有目共睹。在他向诸葛亮传授古文经学之后,为了让他更好地掌握拯救黎民百姓的治政、治军、治国学问,他向诸葛亮引荐了汝南灵山的一位被誉为具有“以蠡测海,深不可测”学问的高人酆公玖,使诸葛亮逐渐掌握了兵法韬略的精髓。至此,他又甘当伯乐荐大贤,向先主刘备成功地推荐了诸葛亮、庞统等风流才俊,于是才有了后来刘备三顾茅庐等一系列三国故事的发生,也才成就了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垂千古史”、“西汉以来无双士,三代而后第一人”之类极尽褒辞赞颂的丰功伟绩。“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他成了精心育人、慧眼识才、举荐诸葛大贤的第一人,也为现代人对于诸葛得以出道“谁为第一举荐人”之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自爱、饱学、识人、育才、荐贤,作为远古之人,真可贵也,实难得也。心怀坦荡,昭示天地,即便司马君生在当代,堪称真君子,也不为过。现在想来,先生司马徽时取“德操”之字,莫非是由于其本人自懂事始就确立了以造就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做人处世的准则了?
玉溪山畔的水镜庄年年如是伫立,水镜庄里的司马徽岁岁如是慈祥,玉溪山脚的小河流日日如是静淌,漳城内外的观光者总是络绎不绝。举世闻名的水镜庄、“妻随夫荣”的玉溪山是不是主要成了外来人考察参观的一道古文化遗址?荆襄人在下大功夫凿通白马洞的同时是否还吃透了司马德操的博大精深内蕴?
外行观其景,内行效其蕴。此为“肥水不外流”!她不应该仅仅只是吸引普天下人度假消闲、旅游观光的一大热点,更应该成为吸引荆襄人陶冶情操、焕发精神的一大亮点。
----------------------------------------------------
那是一个梦,经历了几代人,费尽几代人心血。
那是一段历史,记录了几代人的拼搏,记下几代人的心;那也是一声叹,只留下一个梦······
梦的起点很小,谁也不会想到,在那北方的土地上,那袅袅炊烟源头,那小屋中,梦已经有了萌芽。长辈告诉他,西南方是中原。他站在屋旁的老桑树下,看向西南方,又看看老树,树像小车盖,他决定,他要乘着有这样车盖的车子,驰骋在中原大地上。有人笑他,这是白日梦,他的叔父更是担心带来祸患。她的母亲却支持着他,织席贩履,让他在卢植门下学习,这给他的梦添上第一笔助力。
又是一年春种时,那年,是甲子年。村里有人带起了黄巾,纷纷向中原汇去。动乱起了,乱世来了,他也要向他的梦开始拼搏了。这时,他也遇到了两个为他的梦添了第二笔助力的人。
几年动乱平了,他去了平原,但那不是中原,他的梦也就没有停。几年辗转,金戈又断了几回。胜败又几年,终于,他见到了,那个人——天子。
他到了中原,张开双臂,这是中原的风。但他还没有像那棵树一般的车。他依旧躬耕着,只是在个院子里,就像,或说本就是束缚着,束缚着他的梦。
那天,他收到了一封诏书,他可以去找车盖了,像老桑树一般的车盖。杀车胄,占徐州,刘字旌旗又一次挥动起来。但他没想到,兵临城下之时,似乎清晰了的梦又模糊了。他活下来了,怀着他的梦。
又是几度辗转,旧甲新裂,不得已,他离开了中原,又是一次寄人篱下,又朔望,怎惆怅。
几欲颓废,徐庶却来了,他也带来另一个人的消息,徐庶说他是卧龙。荆州年复年,南雪几重复,茅庐三度顾,草堂先生候。一夜谈,隆中对,谁知天下之计隐山野。也就在那一夜,他的梦再次清晰起来。他也作为他的第三笔助力加入了他。
越来越多人加入了他的梦。他为他的梦,鞠躬尽瘁,付了心血;他为他的梦,当阳桥头一声怒吼,也教江水逆;他为他的梦,千里行,荆州守,怒了山洪,淹了七军;他为他的梦,长坂坡上几度生死来回,殷血染银甲;他为他的梦,弩穿风破,定军山头,亡了妙才;他为他的梦,计指巴蜀,怎奈雒城魂断;他们为了他的梦,纷纷汇聚,金戈铁马,沙场几度生死过,血洒征途。
他走过益州,踏上汉中,东北望,长安,洛阳,就在那,中原,就在那,梦,就在那。似乎伸手就可以抓到了,忽然,一声急报,荆州失守,又一声哀报,益州的水漂了谁的头。
仰天苦叹,剑东挥。一把大火之中,无力的看着,梦,在火光之中,被破碎,泪也干,也难干。一世的梦,还是梦,昔年意气风发今不复,怎奈殷血染白发,剑断金甲穿。
白帝城,他抓住了他,当年的第一第二笔助力纷纷离开了他,他抓住这第三笔助力。泪又怎奈满衣衫。撒手的一刻,他把他的梦托付给了他。
他看向了中原,一颗忠心,前后出师,踏祁山,东北望,便满雕弓如满月,夙夜走笔,一颗赤心谁人偿,鞠躬尽瘁,寒夜英雄又惆怅。
羽扇又轻摇,白发轻拂,五丈原上,病颜泪眼,月半弯,天狼又长嗷。白霓裳,扇轻摇,槊纷扬,星陨八卦阵。
梦还没有断,当年天水的麒麟儿,接下了这个梦。
马长嘶,银枪舞,兵戈东北向。勒马睥睨,少年是否知道,这个梦,将永远只是个梦……
-----------------------
如果你也听说
有没有想过我
想普通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