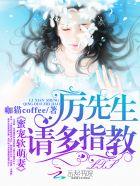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男生为了百合而去变性 > 第7页(第1页)
第7页(第1页)
无人。
当她看到那关了灯的屋子,就这么笃定地想到了。
从前有一天,她的女儿在下着雨的天气里,踩着那雨珠子,蹦蹦跳跳地跑到她院子里,举起手中的纸说道“娘亲,我这个写得怎么样?”,颇有些狂野的字体镌刻在那泛黄的纸张上,那是一首小诗。
夏荷染红烛,珍珠串帘幕。
她摸着还那么天真的女儿的头,对她说道:“你写得真好。”
如今,已是很久了。
唐母敲了敲门,并没有声音,然后她意识着心腹去叫醒了睡在女儿院子中的杂役青奴,推开了门。
静静的,就像她这个人一样,她的女儿慧心。
点燃了还没有烧到一半的蜡烛,屋子瞬间就明亮了起来。
唐母坐了下来,盘问了匆匆被喊醒的青奴,意识她回去继续休息,然后等着她的女儿回来。
期间,心腹丫鬟硬是要给她披上披风,她拒绝了。
“阿笙,等慧心回来再说吧。”
她露出一个寂寥而苍凉的微笑,这使得阿笙不由得一怔,依言闭嘴了。
夜晚的风很凉,那月色也越是缥缈,烛光闪烁着,仿佛随时都要熄灭,却又顽强地站立着。
唐母回想起自己小女儿,那是一个很令人怜惜的女孩儿,是的,女孩,她从未真正长大,只是拙劣地模仿着长辈们。
不久前,有一次,她捡到女儿写下的一首诗,比起小时候要更加顺应心意了,也更加词藻美妙,就如一副美丽的画卷一般。
也难怪老爷要用她的词作,唐母想到,一旁的蜡烛闪了一下。
她是再熟悉不过她女儿的诗词了,小时候基本是都看过,长大后虽然少了,但在那诗词中那股子的悲伤与清冷一直都在。
她在想什么呢?
唐母不明白。
终于,唐慧心回到了院子里,也看到了自己屋子里的光,她一下子就猜到了这会是谁——母亲,也想到了应对方法。
没想到的是,母亲并没有计较她为什么会出去,只是叫阿笙把在炉子上热着的银耳汤端来给她喝。
“慧心,别害了自己。”
她一口一口地喝。
“你毕竟,只是个女孩子,那是容不得污点的。”
唐慧心将银耳汤喝完了。
那双美丽的眼睛就这么淡淡地看着唐母,早已经比她还高的身体笔直地坐着。
这是她的女儿,唐母恍惚了,这又不是她所想的女儿。
不知何时,她所认为的女孩儿已经长大了,与她所想的不一样,根本不同。
“娘,慧心一直都明白。”
“……慧心”,唐母踌躇地道,“若你真要如此,莫要中途折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