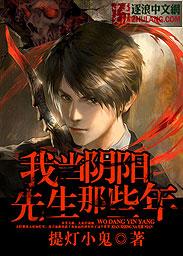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秦朝历史记录 > 第172章 血影惊澜(第1页)
第172章 血影惊澜(第1页)
宜阳城外,秦军营地内一片死寂,唯有篝火偶尔发出“噼啪”声响,似是这肃杀夜空中不甘的抗诉。白骁独自坐在营帐中,铠甲未解,血污斑驳,那柄染血的鱼肠剑就横放在案几上,他眼神空洞地凝视着跳跃的火苗,仿若陷入了往昔回忆的泥沼。
十二岁那年,他躲在草垛,亲眼目睹姐姐被韩军掳走,当作“人牲”钉在祭坛木桩上。姐姐凄厉的惨叫,韩军张狂的狂笑,如噩梦缠绕他多年,复仇成了他活着的唯一信念。可如今,宜阳之战陷入僵局,他心中竟涌起一丝迷茫。
“将军,赵国使者求见。”帐外亲卫的通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白骁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让他进来。”
帐帘掀开,一名身着赵国服饰的中年男子稳步走入,他目光狡黠,拱手行礼:“白将军,久仰久仰。在下赵国使者赵靳,特奉李牧将军之命,前来与将军一叙。”
白骁冷哼一声:“有何事快说,莫要兜圈子。”
赵靳微微一笑,不疾不徐道:“将军,我家李牧将军诚心调停秦韩之战,实是不忍见生灵涂炭。可如今这和谈,还缺将军您的一份助力。”说着,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将军若能在和谈时,应下我赵国一些小小的条件,日后赵国定当助将军成就大业,您这血海深仇,也不愁报不了。”
白骁猛地起身,手按剑柄,怒目而视:“你这是何意?莫要以为我白骁是那为求私利、罔顾大义之人!”
赵靳却不慌不忙,脸上笑意依旧:“将军息怒,您且想想,秦国朝堂之上,对您这位先锋大将可曾全然信任?您为复仇不惜一切,可旁人未必懂您。赵国愿为您提供庇护,给您复仇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白骁心中一震,赵靳这番话,仿若一把利刃,直直戳中他心底的隐忧。他在秦国多年,战功赫赫,却也因复仇手段激进,引得不少非议。可他又怎会轻易背叛秦国?一时间,他陷入两难。
与此同时,宜阳城内,姜芜在临时居所中,对着那半枚刻有“公子虔”三字的残玉发呆。她指尖轻抚着玉面,心中满是疑惑与不安。这玉珏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身世秘密?父亲身为墨家矩子,又为何会与公子虔有所关联?
正出神间,门被轻轻叩响。姜芜警觉起身,低声问道:“谁?”
“姜姑娘,是我,申不亥的侍从阿福。”门外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
姜芜微微皱眉,犹豫片刻后打开门,只见阿福满脸憔悴,眼中透着哀伤:“姑娘,我家将军已去,可他生前一直敬重姑娘,念着姑娘心怀大义。如今宜阳百姓受苦,阿福斗胆求姑娘,在这和谈之际,一定要为百姓争条活路。”
姜芜心中一痛,看着阿福诚挚的模样,轻轻点头:“你放心,我定当尽力。”
阿福刚走,张黻却又带着几名亲卫匆匆赶来。他脸色阴沉似水,一进门便质问道:“姜芜,听说赵国使者去了秦军营地,你可知此事?你与那白骁,莫不是暗中勾结,要将我宜阳拱手送人?”
姜芜心头火起,冷声道:“相邦莫要血口喷人,我姜芜一心只为宜阳百姓,怎会做那等不忠不义之事?赵国使者来意,我与将军一样,也是方才知晓。”
张黻冷哼一声,目光在屋内扫视一圈,似是在寻找破绽:“最好如此。这宜阳是韩国根基,若有差池,你我都担不起罪责。”
和谈当日,城外临时搭建的营帐中气氛凝重。白骁、姜芜代表秦韩双方入座,李牧端坐主位,赵靳立于其后。
李牧率先开口:“今日邀二位前来,只为平息战火,让百姓得以安宁。秦韩两国相邻,多年征战,损耗巨大,实该罢手言和。”
白骁沉声道:“李将军所言有理,可这和谈条件,还需公平合理,我秦军将士的血不能白流。”
姜芜也点头道:“正是,宜阳百姓已受苦良久,和谈之后,需确保他们生活安稳。”
李牧微微颔首:“那是自然。我赵国提议,秦韩以宜阳城外五十里为界,划分疆土,互不侵扰。秦军退至边界以西,韩国补偿一定物资给秦国,以作此次战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