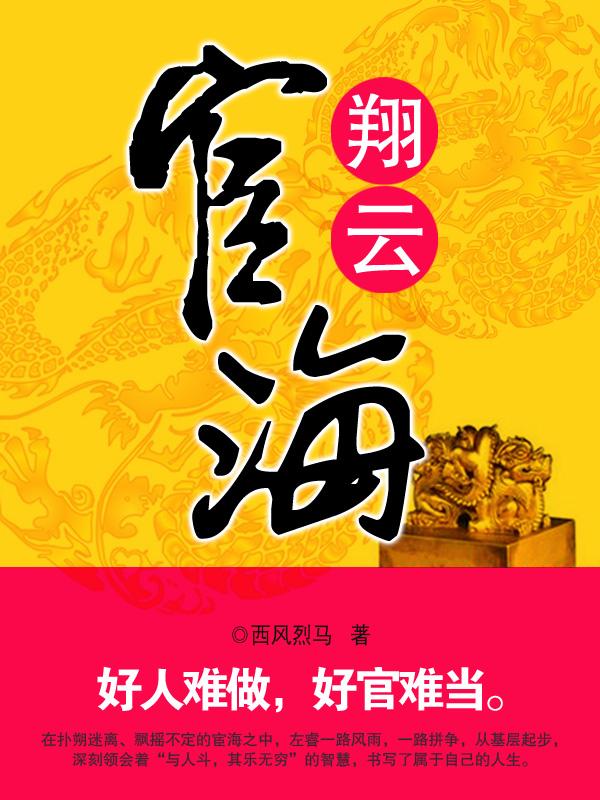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我的一个世纪电影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你讲得对。”我又说:“堂子里姑娘这么坏,说这些话的人,难道都是好东西吗?”
夏之时笑了,他说:“好!我等着你,你赶快去想办法吧!”我走时叮嘱他:“你千万不要上街,外面要捉你的风声很紧,太危险。”当我和他分手时,已近傍晚,我担心他的安全,又怕回去挨老鸨的辱骂,还可能会挨打。上灯时才回到堂子。老鸨两只眼睛瞪着对我说:“局票已经一大堆了。”指责我回来晚了。
第六章求学日本
一、逃跑
我回去以后,装病不做生意。晚上,有许多堂差局票,我一个地方都不去。谁说没有力气,唱不出来。老鸨很惊慌,以为我真的得了什么病。后来看看不像,于是大发脾气,不仅骂我,还要打我。我虽不还嘴,但也不怕,只是哭。我开始用这个办法,好让她们看见我生气,我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她们知道了情况,就指着我责问:“你干吗不做生意?你装病还哭什么?”她们时而软、时而硬地对待我。我知道她们的诡计,我根本不理睬。到后来,哄我也哭,不哄我也哭,就是不做生意。
不管哪个客人来,我都不招呼,老是板起面孔。这样一来,慢慢地生意比较清淡了。
这时,整幢屋里的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说这个姑娘喜欢一位夏爷,夏爷要用钱赎他。
堂子里的人都在七讲八说的。她们看见我这副神气,晓得我不愿再为她们当摇钱树了,很气愤。于是,便开始用压力对待我,并喊了流氓来威胁,我也不理。她们骂道:“你这贱骨头,知不知道你爹娘三百元押你在这里,一百块钱一年,三年还没有满期呢,你想怎样,想偷懒?那不行!”从此,她们就开始凶狠地对待我了。我恨透了,心想:贱骨头是你们自己,整天指手划脚、骂人打人,什么也不做,别人唱得喉咙都哑了,你们只会捞钱、享福、压人欺人,有什么可以神气的?不理睬,也不害怕,我仍旧哭,不做生意,打死我也不做。就这样,看她们把我怎么办。她们用软用硬皆无效果,过了好几天,晓得没有用,就说:“好!好!走!走!走!
你不愿意做生意了,我们送你回家休息、休息再说。”我听见要送我回家,开心死了。我想:“咦!我这个办法想对了,要送我回家了。”哪知根本不是送我回家,而是送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西藏路的一条弄堂里,一座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前楼,他们把我关在里面了。有两个人轮流看守着我,不许见任何人。我又急又气,又难过,想到夏爷在等着我,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脱离这个火坑。每天睡在床上哭泣,两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非常想念夏爷。像这样过了好多天,没有任何人来看我。
自叹命运凄惨,竞落到这种地步,暗想逃跑吧,太危险,如果一旦被抓住性命难保。
那么,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踌躇、徘徊、思绪万千。不!我绝不能继续做一片任人践踏的落叶了。决心逃跑了,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并且着手进行,打扮打扮,梳梳头,穿好衣服,玩玩卅二只骨牌,担任看守的那位四十多岁的男人也过来和我一起玩牌。有时,我叫他弄点酒菜吃吃。他见我情绪好转,看管就放松了一些。有一天,他说:“杨小姐,你乖乖地,大家都很喜欢你,别再这样了。”他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子,以为一用压力就会回心转意,听从他们的话,跟他们走。哪里知道我的主意已定,什么也不能改变我心里积累已久的对这火坑的愤恨,要脱离这火坑的决心。只有什么也不怕,拿出勇气才有出头日子。
有一天晚上,窗外月光明亮,直射房里,似乎在指示我“你要跑,这是好时候”。
那时正当春末,我站在窗口,望着月亮焦急自叹:我完全是为了对爹娘的一片孝心才到这鬼地方来的,现在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月亮呀!请你救助我吧!救助我吧!
过了几天,我就设计故意喝酒、吃花生米,邀那个看守我的人过来一起吃,他很高兴。到晚上11点时候,我对他说:“我肚子饿了,替我买点鸡蛋糕好吗?”我知道一出门就可以买到的,若是路远,他会疑心,不一定肯去,他看我心情好转,很乐意地去了。回来后,看我仍然在玩牌,他放心了。我再请他一起吃喝,到了快2点钟,我又装做想吃水果,水果店离开住处有两三条马路,比买鸡蛋糕的地方远得多,他又高兴地去了。这一回他一走,我就如鱼得水似的立刻把平时用来蒙骗人钱的丝罗绸缎服装统统脱掉,也顾不得冷了,只剩下一套白色的内衣裤。又把金玉耳环、戒指等手饰也都取下来,放在床面前的一张小茶几上,用一只托茶的小瓷碟把它们盖好。我就跪下来,对它作揖、叩头,盯着这些东西说:“啊!我是为了对爹娘尽孝才到这里来的。现在,我要脱离你们,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因此,我一生中对珍珠玉宝首饰从不感兴趣)。于是,我站起来,拿了两毛钱,哆哆嗦嗦地一口气跑下楼梯,奔到弄堂口,赶忙叫了一部黄包车给了他这钱,叫他拉到日租界虹口爱尔近路二号夏爷居住处。在路途上,我顾不得车夫的劳累,直催他跑得快些。一路上,心惊肉跳地老回头张望,看有无追兵赶来。到了四川路,我才稍微平静、放心些。
到了门口那个很了解我们情况的包车夫阿二出来开门,他看见我大吃一惊:“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