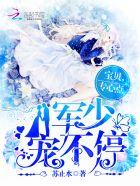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书法家 > 木驴老虎凳鱼目混珠等的虚假与趣难(第1页)
木驴老虎凳鱼目混珠等的虚假与趣难(第1页)
中华文化有两大区系。一系是从实际出发而探究事理性的,另一系是从趣味出发而作调侃。后者不但不具备真实事理性,而且是虚假的事理性,可以说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据说有一种叫“木驴”的刑具,最早的记述是宋代。见于陆游《南唐书。胡则传》:“即舁置木驴上,将磔之。俄死,腰斩其尸以殉。”磔刑,最早是车裂人体的刑罚。五代时把开始设置的凌迟即剐刑,也叫磔刑。可见,是说施剐刑时要用“木驴”。
宋代洪迈《夷坚丙志》卷一《九圣奇鬼》:“甲卒以木驴、石眨、火印、木丸之属列廷下,吏具成案。”但这是说审鬼时先用各种刑具恐吓。后文说,鬼受刑死后,把鬼尸放在篮中,“使徇于庙。相次以驴床钉二男四女及六魈。”对山魈、五通等不存在的妖怪,竟然能用木驴刑具,显然又是虚说。这条文字没有意义。这两条文字都不说“木驴”究竟是怎样的刑具,为什么特别叫这样的名字。
再不见宋代的例证。而元明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却突然很多见。
《窦娥冤》第四折:“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
《赵氏孤儿》第五折:“令人与我将这贼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千刀。”
《生金阁》第二折:“多不到半月时光,餐刀刃亲赴云阳。高杆首吊脊梁,木驴上碎分张。”《酷寒亭》第三折:“上木驴,着刀剐,万剐了尧婆,兀的不痛快杀我。”
《秋胡戏妻》第三折:“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街头便上木驴。”
元代钱霖散曲《哨遍。二煞》:“恼天公降下灾,犯官刑系在囚。他用钱时□□难参透。待买他上木驴钉子轻轻钉,吊脊筋钩儿浅浅钩。便用杀难宽宥。魂飞荡荡,魄散悠悠。”
元代王氏散曲《寄情人。二煞》:“我上船时如上木驴,下舱时如下地府。”
《七里滩》第一折《幺篇》:“拖下龙床,脱了衣裳,木驴牵将。闹市云阳,手脚舒长,六道长钉钉上。咱大家看一场。”
《水浒传》第二十七回:“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
《喻世明言》卷三十八:“任圭自知罪重,低头伏死。大尹教去了锁枷镣肘,上了木驴。只见:四道长钉钉,三条麻索缚。两把刀子举,一朵纸花摇。……前往牛皮街示众。……真可作怪,一时间天昏地暗……少顷,风息天明,县尉并刽子众人看任圭时,绑索长钉,倶已脱落,端然坐化在木驴之上。”
《喻世明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将三人押赴木驴上,满城号令三日,律例陵迟分尸,枭首示众。”
蒲松龄《聊斋俚曲集。增补幸云曲》第二十八回:“江彬喝道:‘好贼泼贱人!你得罪着万岁了,给你木驴骑着哩!’剥去了大姐衣,碎锣响破鼓槌。人人要看狼心肺。……登时剐了个粉粉碎。一霎时油头粉面,只剩了白骨一堆。”
可见例句却仅见于元曲和后来的小说,也都没有关于形制和得名原因的说明。
明代陆嘘云编《世时通考》开始了辞书对此词的著录。此书国内失传,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所编《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收有万历中谭城余云坡梓行《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时通考》上下二卷。卷下《讼狱类》木驴:凡犯剐罪者上木驴。”也是从文学作品而总结的,没有解释。
但奇怪的是,到了今人却有了更具体的说明。现按时间顺序引录于下:
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年):“古代一种惨酷刑具,在执行死刑时,把罪犯钉于木驴上游街示众。”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1984年):“是封建时代一种状似驴形的木制刑具,执行剐刑时,先将受刑者绑缚其上,游街示众。”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在《赵氏孤儿》中注:“古代一种布满铁剌的木制残酷刑具,木架下装轮轴。用刑前先让犯人骑在上头,游街示众。”
王季思等《元杂剧选注》:“固定犯人手足的木架,是古代执行剐刑时用的。”
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1985年):“有钉的横木轮架。亦称驴床。剐刑时,将犯人卧于床上,游街示众。”
胡竹安《水浒词典》(1985年):“乃装有铁剌的木桩,下有轮子,形状像驴马。”
《喻世明言》陕西人民出版社注本(1985年):“一种装有轮轴的木架,罪犯在受凌迟前,都要先骑木驴游街示众。”
《汉语大词典》第四卷(1989年):“为装有轮轴的木架,载犯人示众并处死。”又,“驴床:古时一种刑具。有钉的木架,剐刑时,将犯人钉在架上处死。”
王起主编《元明清散曲选》(1990年)对钱霖例注:“元代有一种酷刑,把罪人钉在四脚凳上陵迟处死,木驴即指这种凳子。”
《聊斋俚曲集。增补幸云曲》邹宗良(1999年)注:“一种刑具。其制为装有轮轴的木架,可将犯人钉于其上示众并处死。”
这些解释差别很大。或说像驴形,或说像驴马形,或说是凳子。多数却不说像什么,而说“骑”在上面。或说“布满铁剌”而可骑;或说是“装有铁剌的木桩,下有轮子,形状像驴马”,然而,这样的木桩实在不能像驴或马。或说是“木架”而可骑。或说把犯人捆绑于上,或说钉于其上,或说卧于其上。互相矛盾。罪犯在受凌迟前游街示众,为什么要骑木驴?又都没有说犯人骑木驴有什么痛苦;又不是刑具,而是运载工具。而无论哪种解释,一概不交代他们那样解释的根据是什么。这里决没有什么不可泄露的“天机”,只能是并无根据的想当然罢了。
各种解释唯一共同的地方,是说用于剐刑。但这是一些例句中已经说明了的。
民间群众还有一种更为奇怪的说法。木驴,是专门用于淫妇的。是按有轮子可行的木头驴,背上有一长柱,让淫妇坐在上面,使那长柱穿入她的**。如此游街示众。笔者在陕西、甘肃都听到这样说法。《运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李安纲《古宫刑考》:“大约在明、清时代,统治者发明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刑法,即让那些女犯骑在一具木驴上,一根木柱直捅**,还要牵出去招摇街市。”可见山西也有如此传说。而前面元明两代的例句却多是用于男性。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刑具的话,自然应当有其他历史性质的实际例证,而不会只见于文学作品中。把刑具特意做成驴形,实在没有丝毫的必要。所以,“木驴”只能是“文学语言”,而不是记实的名物词。
木驴是用于剐刑,自然要把受刑人在某种支架上捆绑牢靠。《宋史。刑法志一》:“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刑也。”明刊本《全相花关索贬云南传》有凌迟的插图:立有两桩,上部有环,各栓一犯人辫子,倮身。两臂平伸,被绳索捆绑。《汉语大词典》“凌迟”条附有此插图,可参看。可见,并没有被那样解释而叫“木驴”的刑具。
“木驴”它究竟指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名字,还需要重新研究。
可以确言,“木驴”的“木”,应当是泛指刑具,是平实的说法。古代基本刑具多是木制的,如木棒、木钩子、木枷、木手铐。所以“木”可以是刑具的指代说法。《周易。蒙卦》:“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孔颖达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列子。列御寇》:“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郭象注:“木谓捶楚桎梏。”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其中的“木”指“三木”,即加在犯人颈、手、足的刑具。《汉书。司马迁传》:“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颜师古注:“三木,在犯人颈及手、足。”
“木”也可以是“目”的谐音:条目。指按刑法的某一条某一款来定罪。
而“驴”是“律”的谐音,却是故意作趣而难的说法。“刑”与“律”相关。受刑也就是受律。刑场也叫法场。把判罪意思的“受刑律”,变说成“受木律”,再经谐音,成为“受木驴”。
执行剐刑需要立木桩。这样的木架可以用“床”来说。《汉语大词典》“床:安放器物的支架、几案等。”“床子弩:带木架的大弩。”
对罪犯游街示众,是要人们亲自看到犯罪处刑的下场。把“看到”用文言文来说,就是“寓目”。把“寓目”两个字打颠倒,成为“木寓”,也就可以谐音成为“木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