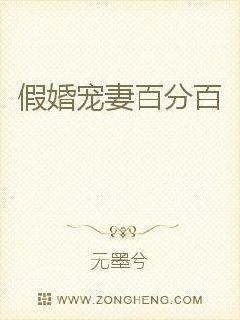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和平精英酷二狗传奇 > 第三十章 将计就计(第1页)
第三十章 将计就计(第1页)
晚上八左右,酒吧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因为还没有到黄金时间,人还并不是很多,比较安静,也因此感觉多了一分宁静。袁淳从三年前在南京因为义父罗叔的关系在密码酒吧帮忙到如今闻名杭州的夜场皇后,这是一种蜕变,属于袁淳一个人的改变。酒吧里的背景音乐突然低了下来,在众人左顾右盼以为出了什么事地时候,袁淳已经走上了酒吧里空出的那一片表演舞台。台下众狼友见状压抑不住心中狂喜,顿时酒吧里此起彼伏的口哨声四处响起,好不热烈。袁淳不是没有在酒吧里表演过,只是次数很少,平常虽是带着笑脸,但谁也能感觉到她的冷漠,今晚好不容易又有这个机会,盯着袁淳不是一天两天的狼友们心里又怎么会不激动。袁淳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台上,一身合体的浅蓝色连衣裙更显一分清纯,多绕。没有打招呼,没有问候,轻轻一曲欧美女歌手giulia的cefrumoasaeiubirea缓缓唱出,歌声轻快带忧郁,自然淳朴的曲风,袁淳投入的演唱,征服了台下所有人的耳朵。
陈浮生靠在二楼的扶手上,看着台上的袁淳,低声感叹了一句又是一朵花成熟了。随意的瞄一眼楼下两三张桌子并拢坐在一起的十来个人,眼神微眯一下便不再关注。
陈浮生转过身来对正投入欣赏袁淳演唱的王玄策道,“要不趁现在还早,我带你去老城区逛一下?就当是欣赏下月色也好啊。”王玄策略带深意的看了一眼陈浮生头称好。陈浮生带着王玄策出了酒吧大门,陈庆之和周雀已早早的等在门口。
四人并没有坐车,只是闲散的徒步闲逛着,并非真的要去老城区,走到哪里算哪里。
王玄策抬手扯下身旁树上的一根弯下来树枝上的树叶笑着问道,“都看出来还敢离开,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
陈浮生淡笑道,“我们晚上要是不离开,那些人又怎么敢放手做呢,怎么也得给他们一发挥的空间不是。”
王玄策眼眸一亮问道,“知道是谁?”
陈浮生摇了摇头道,“就是不知道,才要让他们做出来,只要有动作,那就一定有漏洞!”
酒吧内,原本静谧放松的酒吧氛围,被一声酒瓶落地后的碎声打破。源头来自陈浮生离开前关注的那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倒也生猛,打完服务员二话不就开始扔桌砸椅,一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表情狰狞的比遇见了杀父仇人还要恶上三分。
原本坐在旁边的人早已起身,很配合远远站到一边看着十来个人卖力的表演着。远处的樊老鼠就静静地半蹲在那里,嘴上叼着一根烟自顾自的吞云吐雾,看着那十来个人演猴戏。
一支烟吸完,樊老鼠恋恋不舍的最后吸了一口烟屁股随意将烟头弹在了地上。起身,拍拍身上落下的烟灰,缓缓向闹事场地走近。
十来人中的一个壮汉朝身边的人打了个眼色,意思是心,这是个硬茬子。眼色还没有打完,身旁的众人也还没来得及完全接收老大眼色传来的关心。樊老鼠走近不管三七二十一,单手一握壮年男子的胸口衣服,抓起,用力甩向另一侧的墙壁。壮年男子吐了一口血水,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用不上力,只能任命的背贴着墙壁恢复着元气。
旁边看戏的众人包括场中闹事的几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暗道生猛。一想到那壮年男子的后背,下意思的身后摸向自己的后背,想想就要打颤,后背一片冰凉。樊老鼠一手解决一个,没有出现什么旗鼓相当的战斗场面,完全是一边倒,打的闹事的犊子们东一个西一个倒在地上,哀声遍地。樊老鼠看着场内怂了的几人撇撇嘴,随意道,“还有谁要来?咱比划比划。”场内的一帮闹事的被樊老鼠这一手镇住了,连自己的头儿都被人轻松拿下了,自己还拿什么去跟人家拼。拿义气?算了吧,这话哄哄初入江湖一身方刚血气的年轻人还可以,愣头青的只要老大喊一声上,便恨不得立马为老大舍身取义的往上冲去了。都是江湖上的老人了,谁唬谁啊!
站在楼上的陈园殊不悲不喜,表情淡定,似乎楼下只是在解决一些纠纷般不值得一提。朝樊老鼠扬了扬下巴,希望速战速决。
樊老鼠找了张凳子随意坐下,闷声道,“我也不为难你们。其余的都可以走,留下一人我问话。留谁,哥几个商量着”。
闹事的几人脸上的表情比死了娘还要难看,本来是来踩人,哪知道反倒被人踩了,几人对视一眼,又回头对着那靠在墙边休息的领头深情对望了一眼,便义无反顾,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头不带任何眷恋的出了大门口,转眼便消失在了街口。
陈浮生掏出震动的手机接了一个电话,嘴角扯起一笑意,了声知道了便挂了电话。冲着王玄策几人玩味道,“鱼儿上钩了,我们也回去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夏日的晚上,一阵清风吹过。王玄策抬头看看天上快要被乌云遮住的明月叹了一句,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四人慢慢走在回去的路上,前面一人在夜风中萧瑟的靠身旁的一根电线杆上吞吐着烟雾,任由月光在地上拉起一条身影。陈庆之与周雀顿时警觉,配合的走到前面一左一右将陈浮生围在中间。
陈浮生诧异的看了一眼笑道,“朋友,让个路?”
一头火红妖异的长发披在肩上,任由晚风吹起,带着一股邪气,浑身健壮的肌肉在紧身衣的束缚下隆起,欲有挣脱之势。
年纪大概在三十岁左右的男人随手弹走烟头,头也不抬的冷漠道,“今天,你还是留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