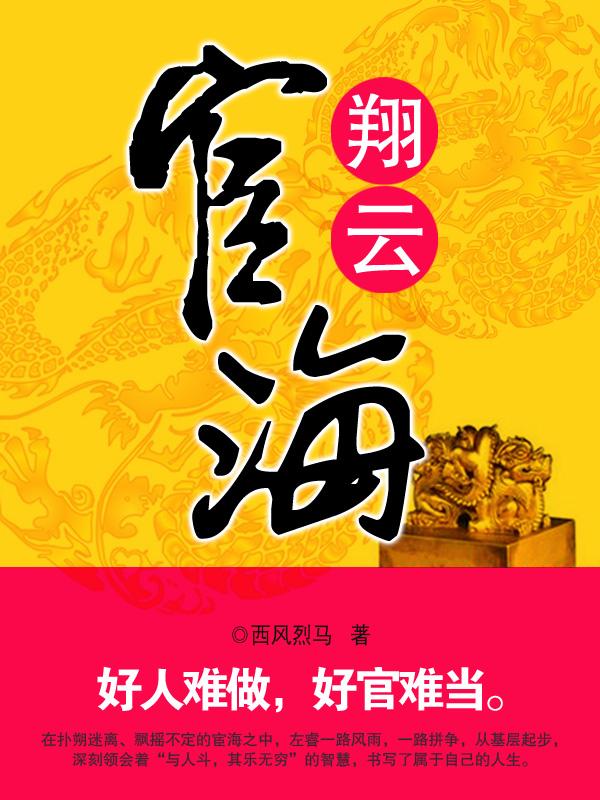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喜耕田的故事在山西哪拍的 > 第288节 针锋相对(第2页)
第288节 针锋相对(第2页)
“不辞就不辞,干嘛说得那么难听?我不就是偶尔出宫玩一玩嘛!”
“玩一玩?”裴子墨冷笑,“臣食君之禄,就要忠君之事,公主与其私下游说臣行杀头之事,何不自省皇上为何为公主做此安排?你刚才也说了,东周朝历来都是公主随太傅学习到十三岁为止,那公为何公主已经十六岁了,皇上还要专门为您请个太傅授课?公主是不是要自省一下?”
说到这,龙馨瑶已经很确定这位状元郎,对于担任她的专任太傅有多么的不满了,可她满肚子的委屈又到哪里去说,这还没开始授课,他就视眼前的公主如此不敬,还不知道日后的早课,他如何为难自己呢。越想火气越大,不由尖声道:“裴子墨,你是在笑话本宫嫁不出去吗?”
对于她的凤目圆瞪,裴子墨并不以为然。他巴不得这位千娇万宠的公主哭着跑去找大玄皇帝,说她很讨厌这个太傅,让皇上赶紧换人呢,若是真能如此,那就两下清静了,各走各的道,互不牵扯了。于是出口的话,就比想象中的还要难听。
“公主,不是我说你嫁不出去。而是事实摆在眼前就是嫁不出去。而且你自己也说你已经十六岁了。公主既然识字,那大可以翻开皇家史册看一下,东周建朝两百余年,哪一个公主不是到了十二三岁就被王公贵族的公子们排着队的来请太后。或皇上赐婚。又有哪一个十六岁还未出嫁。恐怕人家那些公主十六岁的时候,孩儿都已经好几个了。再者又有哪一位公主就算是皇上赐婚,人家那些公子们都想着法子的拒绝的,还有……”
“够了……”这一下龙馨瑶的腮帮子都被他气鼓了。这厮的话是越说越过分。
“公主还是自省一下吧!”逮着空,裴子墨还是不知死活地补充了一句。
“自省?”龙馨瑶的两条柳眉微微蹙起,语气已经十分不悦,“裴太傅,请你说话自重,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何况本公主从来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需要自省的事。而且父皇只是任命你做我的太傅,教我学问,可没让你这么奚落我,我要是将此话告诉父皇,你该知道后果如何?”
“做学问之前。需先知礼。”裴子慧毫不畏惧她去告御状,义正辞严,“我做为你的太傅,教你学问之前,就是要先教你知礼学规矩。再者公主视规矩为无物。经常偷溜出宫已经很不成体统,还不分时间场合的到处乱闯,在大街小巷留下一段又一段‘故事’,敢问公主,你可曾耳闻有哪位公主做出你这样的事了,这不需要自省又是什么?”
这一会儿,裴子墨把心中的隐忍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笑意,反而那一本正经的陈述,似乎更加确实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龙馨瑶不满到了极点,咬牙道:“什么连中三元状元,什么谦谦君子。我看你说话尖酸刻薄到如此程度,也不过是图有其表罢了。当一个三岁孩童的师傅还差不多,当本公主的太傅果真是有些勉强。再者本公主什么言行举止与你何干,连父皇都没管我,你凭什么管!”
“以前与我无干,以后就有了!”裴子墨道:“再者皇上怎么没管。若是真不管,那就任凭你这样放任下去了,正因为管了,才请了我这个太傅。再者我该做三岁孩童的师傅,还是做你公主的师傅,这都是皇上一张圣旨决定的,你这是在说皇上他目光短浅,有眼无珠吗?”
“你!”龙馨瑶呼吸一紧,再无反驳之词,只瞪眼跺脚道:“裴子墨,我就是出宫玩一玩,你何来这么多的说教之词,何况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有要紧的事。”
裴子墨的目光就有些难以置信,“要紧的事?你的要紧事就是给皇家蒙羞吗?”
“你说什么?”龙馨瑶终于忍无可忍,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她身子扭了扭,双手在空中乱抓一气,终于抓到几片已经枯萎的叶子,就朝裴子墨丢了过去。
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什么了什么,害得大家都如同对待仇人一般对她待。淑妃和荣妃这样说她,她理解成那是父皇太过宠爱她,所以她们针对自己,也顺便算是打击皇后。所以她不以为意,可裴子墨呢?他为什么如此羞辱自己,就因为他不愿意当自己的太傅,难道已经不愿意到这种程度?
“公主,可怜天下父母。皇上虽然是九五至尊,但疼爱儿女的心情和普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望你体谅皇上一片苦心,好好在宫中反省,日后不要再做出有辱皇家颜面之事。臣告退。”
裴子墨一拱手,头也不回的走了。
留下僵硬在此的龙馨瑶,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良久之后,她终于蹲下身子,双臂抱住自己,眼泪扑籁籁地落了下来,哭够了才喃喃道:“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