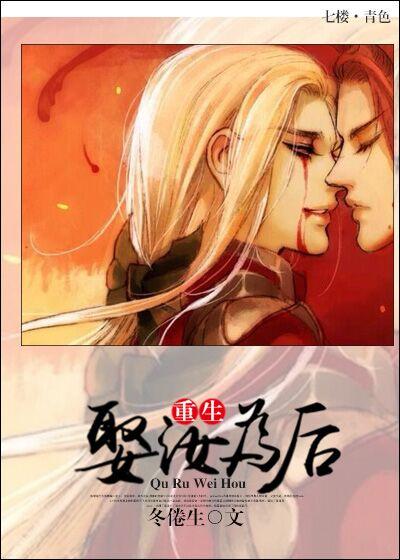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太子殿下要我 > 第123章(第1页)
第123章(第1页)
她不介意他是否真的察觉,她只要他一念之间的决定,最后的决定。
之恩微垂着眉眼,浓黑的睫毛覆盖了他眼底的情绪。思影说完了,可他很久都没有说话。
思影心下不安,身子从他怀里扭出来,睁大一双泪眼望住他,“你不信?”
他又沉默了很久。在思影的印象中,他们在一起时,不管她说了什么,他从来都没有沉默这样久,她完全听得见他有些混乱的心跳,也能感受到那心跳背后的重重疑云。
他终于开口,却不是回答她的问题。他反问她:“那,你真正的心里,是如何看待我的?”
她稍事低首,两大滴眼泪恰到好处的滑落,“我虽然身不由己,时而言不由衷,但我待殿下,却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他似乎有些颤抖,抱住她的一双手臂拢得越发紧了,喷在她头顶的鼻息也有些局促而紊乱……思影闭目感受他的温热气息,可她从来没有觉得他的心思如此难以捉摸,他沉默的每一刻都令她煎熬得有如凌迟,仿佛是在等待最终的审判。
良久,他将轻轻她放回榻上。
“我知道了。”他低声道。
他低下头,细细的、慢慢的替她掖好被角……
“我立刻通知刑部,速拿纪绅归案。”
———
和纪绅的诏狱比起来,刑部大牢要温和许多,至少名义上,是得依着规矩来审,不如诏狱那般肆意妄为,惨无人道。
但执掌刑部的人——是马仁。
思影想,以纪绅和马仁平日的恶劣关系,纪绅落到马仁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马仁悄悄来问过之恩,说纪绅这厮性子极野,肯定不服刑部审讯,可不能让他满口胡说八道徒惹麻烦,要不然,先割了他的舌头?
之恩听得头皮一麻,“让他闭嘴有很多办法,一定得割舌头么?”
思影服了程太医精心配制的药,又闭门静养了两三日,略略养了些精神,听说纪绅已被拘入刑部大牢,便支撑着起身整衣,告诉之恩:她得去见一见纪绅。
……
刑部大牢设于暗无天日的地下,虽不及诏狱那般神秘诡异、煞气骇人,然而牢里弥漫的浓重血腥气,较之诏狱,似乎也并不肯落了下风。
思影隔着高耸森严的铁门,沉默的望着不远处的纪绅——他此刻被高高吊着,蓬头垢面的脑袋斜斜折向一边,一大把黑色布条横穿过他的口角,紧紧勒得他面目扭曲;手脚分别用好几具镣铐死死锁住,约是他挣扎得太厉害,脚踝、手腕处,都磨出了森森的白骨。
思影心中涌起几分感慨,长久以来,她困于眼前这个人的胁迫、控制和欺骗,她曾因无力反抗而恼恨,也曾在洞彻其阴谋后痛苦……她曾经那么多的希望和绝望,都因此人而起。
但这一切都结束了。眼前这个人,终于、再也,无法威胁到自己了。
狱卒取了钥匙开门,上前拿下纪绅口中布条。思影这才发现他口中除了那一团黑布条之外,空隙部分还用棉花塞满,使他非但言语不能,连正常闭合口齿都无法做到。
狱卒们手脚毛躁,胡乱抓扯之下,松散的棉絮飞入咽喉,呛得纪绅撕心裂肺的不住咳嗽。
思影微微蹙眉,示意狱卒们退下回避。
纪绅垂吊着头颅,猛烈咳嗽好一会儿,方渐缓了几分气,眼皮一撩便看见了近在眼前的思影。
他顿时暴躁起来,一双黯如死灰的眼睛猛地燃起灼灼烈焰,枯槁般奄奄一息的躯体癫狂般躁动,扯动身上铁索哗啦啦的响,似要将那束缚全身的铁链全部狠狠的掷向她:
“贱人!”
他用尽全力吼出的声音嘶哑如破锣:“忘恩负义的贱人!我何时对你用过寒食散!你血口喷人!”
思影站立不动。哪怕此刻近在咫尺,他一身蛮力再也无法威胁她分毫。她淡淡道:“纪大人莫要激动,真相如何并不打紧,太子认为你做了,你就是做了。”
纪绅双目圆瞪,眼中喷薄的恨意如赤红烈焰,“你竟敢陷害我!别忘了是谁带你来到京城!是谁帮你接近太子!”
“是你。”思影道,“是你带我来到京城,为了你不可告人的目的,处心积虑安排我接近太子……我都告诉太子了,太子大为生气,这才非要拿办你不可……”
纪绅目中两簇赤焰倏忽闪跳,须臾,渐渐慢慢的沉寂下来。
“我低估你了……”他哑着喉咙道,“宋子诀、宋书洪、马仁、程太医……还有谁?真是无所不能啊你——”
他暗哑粗粝的嗓音听来如老鸹一般阴鸷:“太子以为你是什么好鸟,才这样帮你……你别太得意,太子眼里揉不得沙子,等他有一天知道你如此阴险不择手段,你看他还会不会跟你站在一起,还会不会拼命护你!”
纪绅忽又大笑起来,狂肆的笑声配上他破锣嗓子,听来炸耳且悚然——
“你以为太子真像你想的那么蠢!他心里亮堂得很!你这般利用他,你真当他一点儿不知道!不过按下不表,等秋后算账!你算什么玩意儿!仗着你那副身子骨到处和各种男人秽乱,讨换好处!待太子知道真相,你以为他能饶得了你!由得你这居心叵测的女人在朝堂兴风作浪!”
纪绅越发骂得不堪,思影听得心中烦躁,“那你去告诉他吧,现在就去!”她冷冷道:“你知道得再多,也不会有机会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