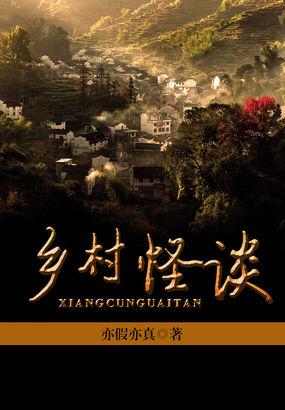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青云俏美人李泽 > 第895章 错有错着(第3页)
第895章 错有错着(第3页)
可眼前这截裸露的肌肤,竟是光洁无比,莫说那般严重的伤疤,便是连一丝细微的瑕疵也无。
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窜入杨炯脑海,他瞬间如遭雷击,手上的力道不自觉地便松懈了几分,失声惊问道:“那墓中之人……不是你?!”
李溟正自拼力挣扎,忽觉身上束缚一松,又闻此问,那满腔的委屈与怒火更是如同找到了宣泄口。
她本就觉得杨炯是那负心薄幸之徒,枉费自己先前还对他存有那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如今更是百口莫辩,悲从中来。
当下眼眶一酸,那强忍了许久的泪水险些便要夺眶而出。
可她性子何其刚强,硬是死死抿住了略显苍白的嘴唇,猛地别过头去,不去看杨炯,只用那头泼洒下来的银白长发对着他,随风微微震荡,平添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倔强与破碎之美。
杨炯见她这般情态,心中疑窦更是如同野草般疯长。
他当即站起身,目光如炬,死死盯着李溟大腿那原本应有伤疤的位置,几步抢上前,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冷厉与探究:“我说当时李泽自刎之时,为何对你……不,对那‘李溟’未留一言,而那‘李溟’对李泽之死亦是毫无反应!当时我只道是你们自知兵败,心灰意冷,无话可说。如今看来,那军前饮毒之人,根本就是你的替身?!”
他越说越是觉得脉络清晰,许多当时被忽略的细节此刻一一浮现眼前。
不容李溟反应,杨炯竟又猛地俯身,伸手便要再去掀李溟腹部的衣衫,他记得那替身腹部也曾受过箭伤。
“你干什么!!!”李溟又惊又怒,双手急忙护住身前,瞪眼怒吼,声嘶力竭。
“不许动!”杨炯此刻心绪激荡,只想印证心中猜想,见她反抗,语气更是冰冷慑人,眼神锐利如刀,竟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势,“再跟我耍性子,小心我把你吊起来打!”
李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凶狠模样吓了一跳,竟真的怔住了一瞬。杨炯趁此间隙,手疾眼快,已撩开了她腹侧的一角衣衫。
目光所及,只见那腰腹间的肌肤平坦光滑,紧致有力,同样是没有半点伤痕。
杨炯直起身,死死盯着李溟那头标志性的白发,脑中思绪急转,许多前因后果瞬间贯通,不由得喃喃自语道:“是了!是了!怪不得当时张肃一力主张乘胜追击,渡过大雪山,直捣孔雀帝国国都,你却千方百计阻拦,甚至不惜动用主帅权限禁止他调兵。
原来你本意并非怯战,而是想尽快稳住南疆局势,逼走处处掣肘、紧盯着你不放的张肃,好趁机脱身返京!”
然而,一个新的疑窦随即升起,杨炯眉头紧锁,追问道:“不对!即便如此,你为何不将那替身留在军中坐镇,自己先行回来?何至于拖延至此,酿成今日之局?”
李溟听他问到此处,满腔的悲愤与无奈终于爆发。
她猛地从地上跃起,也顾不得衣衫狼狈,对着杨炯大吼道:“你当我愿意吗?!你派来的那个监军张肃!一来便断了我的军饷粮草!军改之后,一切军资调配、军功核验皆需经他之手!
这还不算,那混蛋时刻派人如同影子般盯着我,名为辅佐,实为监视!我敢轻易离开吗?!”
她越说越是激动,胸脯剧烈起伏:“当时南疆战事正是千钧一发之际,孔雀帝国联合周边四国,五路大军压境!那替身虽与我形貌相似,于军务也熟悉,可临阵指挥、随机应变,岂能及我万一?
稍有不慎,行差踏错,便会被那张肃抓住把柄,参我一个临阵脱逃、指挥失当!到那时,我多年心血经营的朱雀卫,岂不是要彻底落入他手中?!我……我如何敢冒此奇险!”
杨炯听得此言,心头猛地一凝。
原来如此!
自己当初只是嘱咐张肃要看紧李溟,莫要让她轻易卷入京城是非,没想到这小子竟是这般“恪尽职守”,给了李溟如此巨大的压力,大到她不敢离开军营半步,甚至随时可能失去对朱雀卫的控制权。
转念一想,李溟当时处境确是两难:既要保住朱雀卫这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又心系京城兄长安危,想要入京援手。
权衡之下,她只能行此险招,先让替身回京,自己则试图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速战速决,解决南疆战事,再图北上。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她恐怕也未曾料到孔雀帝国竟会联合诸国大举来犯,使得战局胶着。
而她禁止张肃冒进,一方面确是稳妥之策,另一方面,恐怕也正是要激得张肃这血气方刚的年轻监军按捺不住,自行其是,她便可寻得脱身之机。
张肃果然中计,愤而离去蒲甘国“借兵”,倒是阴差阳错,给了李溟金蝉脱壳的机会。
一念至此,杨炯心中也不知是该感叹造化弄人,阴差阳错,还是该念一声命运无常,错有错着。自己当初随意布置的一步闲棋,提拔的一个新科探花,竟在千里之外,引动了如此巨大的波澜,造成了这般预料之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