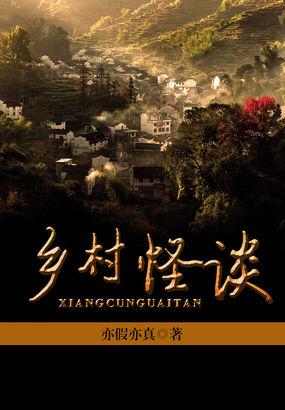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开局山寨小喽啰 > 第242章 吏禄六百石(第2页)
第242章 吏禄六百石(第2页)
李大狗苦笑一声,望了眼河对面,颇为自嘲:
‘或许我应该从县城方向过来……’
当下迈开脚步,往村口走去。
大概是李有宗走远了。逐渐又有声音,切切而起。
李大狗看见有一个叔辈的妇人,不屑地啐了一口:
“神气个劲……吃完今年,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年……”
另一个脸上没肉的妇人,咧着嘴附和:
“就是,富贵命哪有那么好享,说不定啊,二狗子就是这么被克死的……”
先前那个妇人,“呼”得一声,醒了把鼻涕,往身后的石碑一抹,恨声切齿道:
“你还别说,二狗子多半是冤死的,要不怎么会来找他奶诉苦,还把他奶带走了。”
“天要黑了,这话可不兴说……”
————
李大狗的脚步猛然一顿,停在了她们身旁,目光也是呆愣地望向右侧第五栋房屋。
暮光之下,屋舍墙体粉刷一新,门前也扎起了一圈篱笆,半人高的院门左一侧,突兀地挂着一节草绳,而另一侧,还贴有一张斑驳发白的符纸。
这是有家人去世的标志。
观其分化程度,大概已有半年多了。
李大狗深深叹了个气,想起了那个有些迷糊,又很是偏心的奶奶。
当下并未搭理这些说长舌之人,沿着小路跨过还未关闭的矮门,步入了院墙之内。
放眼望去,白墙黑瓦之间,悬挂着几排饱满的花生,鲜红的辣椒,和几串新晒的腊肉。
李大狗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亲近之人的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总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
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襄国朝廷,虽说自己也抓了几个通缉犯,但总体而言总感觉亏欠了点什么。
然后转头就看到院角位置,堆积成垛的牧草,累成两人多高。
他的笑容莫名变得有些不自然了,有时候家人对子女的期望太深,也会变成一种负担。
他只能微微叹了口气,沿着铺过细沙微微垄起小径,往客厅走去。
身后突有脚步声传来,转头看时,就见到父亲李有宗手拿锉刀和曲刨回来,身后还跟着一脸不太情愿的李小妹。
李大狗向侧边走出几步,好避开了他们的必经之路,再仔细看时才发觉,昔日那个黄毛丫头,而今不但面色红润了许多,就连身量也长高了两寸。
头上虽还插着自己削的那只枣木簪子,身上的衣服却是今年新做的,虽然在尺寸上依旧稍显大些,却已经看不到补丁了。
两人从李大狗身边默然经过,行至屋檐下时,小妹被父亲赶进了厨房,后者从客厅门后,取出了一根未完成的毛竹扁担,一屁股坐在门槛上,用锉刀继续削制。
富有节奏的刨锉声中,刚进厨房的小妹,再次迎来了母亲的训斥。
大抵是让她少往外面跑,一天天找不见人,没个女孩样……
小妹自然也不服气,嘀咕道自己拾柴拔草都做完了,刚有时间找小伙伴玩,就被爹逮回来了,太不讲道理……
李母本就不是能言善辩之人,长辈们的龃龉也不好说给小孩子听,被她几句话挤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只好咚咚两下,在她脑袋上敲了两个板栗,恨声道:“你给我省点心吧,别让你大哥回来看到你没有长进,还是一副野丫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