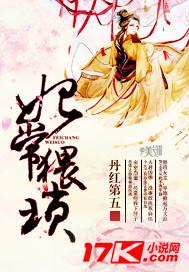玫瑰果小说>刘瑞明文史述林 > 庐山远公话校注商补(第2页)
庐山远公话校注商补(第2页)
校注:“无量无边义”,“义”上原有“宜”字,当因与“义”音近而衍,今删。
按,问题之一是“无量无边”特加引号,并无什么特殊含义。如此,反而成为,知道一句佛理,就分别得到另一种叫“无量无边”的佛理。实在是不知所云了。论题是“化生”,即向各种而无边无量的人平等传法。前文对比的“湿生”是:“如是之人,多受匿法,得一句一偈,不曾说向诸人,贪爱润己,不解为众宣扬。”据此,后“得”字是“向”字之误。问题之二,原卷的“宜”却应是“宣”之误。问题之三,“文牵教化”意不通畅,“牵”当是“迁”字成误。综此三点,议句前半处当校点:“得一句妙法,分别向无量无边,宣义文,迁教化。”问题之四,后处宜细致校补为:“如然一灯于十灯,亦〔于〕百灯、于千灯,亦〔于〕百千万亿之灯。”
262-21是事不于身心。
校注:于:动词,义为“居”、“存”。曹植《来日大难》:“广情故,心相于”即其例。下文“相公在于”,“在于”为同义连文。
按,所注误。“于”在古今都只是介词,后必带所介引的宾语,没有在“介”字后止逗的。“于”从无动词的用法。曹植例,“心相于”实是“心相与”的别写。“相与”为词,本指相处、相交,因而引申为情厚,或指情厚的人,不烦示例。至于“相公在于,座主莫谩主人,但之好好立义将来,愿好相抵对。”(2654)其中“在于”,却是“在此”之误,《校注》失校。试对比264。10:“相公在此,上人若垂大道,立仪将来,不弃刍薨,即当恩幸。”即前句中“义(仪)”之误也失校了。回到本条议句上来,原“于”字本作“於”,所以实是“放”之误。“万法皆虚,何曾有实?东西无迹,南北无纵(踪),是事不放身心,一体迥超三界。此即名为无相。”这样才文从字顺。
1当信即有,不信还无。万法不于心身。此即名为非有相。
按,“于”同于前处,是“放”之误。
2人生在世有身智,浮名为二足。或即有身而无智,或即有智而无身。只此身智,不遇相逢,所以沉沦恶道。身智若也相逢,便乃生于佛道。
校注浮”,疑当作“呼”。
按,此段文字疑点多有,要细作讨论。首先,“身”即身体,但有的人怎会只有智而无身呢?“身”字大有疑。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二足:〔术语〕以人两足譬福、智二者。六度中般若为智足,其徐五度为福足。《义楚六帖》一曰:《智论》云:‘佛积万行于三大劫,福足智足,无间无遗。’”另有“福足”、“智足”条,不烦具引。这充分证明,议句中很多“身”字必是“福”字之误。“福”,底本如果别写为“孚”字而作行草书,后之抄录者误成形近的“身”。所以,原有的“浮”也应是“福”之误,不当疑为“呼”字之误。这段文字应校为:“人生在世,身有智福,名为二足。或即有福而无智,或即有智而无福。只此福智,不相遇逢,所以沉沦恶道。福智若也相逢,便乃生于佛道。”
263-5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身恨智生迟,智恨身生早。身智不相逢,曾经几度老。身智若相逢,即得成佛道。
按,各句中“身”字都应校为“福”。“智生福已老”言福已快结束。
263-7有此身智,此即名为二足。
“身”仍是“福”之误。
8第十无足者,虽即为人,是事不困,不辨东西,与畜生无异。
校注:“不困”费解,当为“不会”、“不明”之类。
按,但“困”无从有“会”或“明”之义,也不会成此误。实际“不”是“亦”形近之误,敦煌抄卷例证甚多,恕不赘。
12佛法难思,非君所会,不辞与汝解说。
校注:不辞:即便,纵然。
按,“不辞”无从有所释之义。不辞,即不说,指不能。杜甫等唐诗、禅僧灯语、变文等多见。详见拙文《“不辞与汝道”与禅家不立文字》,载《文史》第44辑。
14维那检校,莫遣喧嚣。听讲时光可昔(惜),汝不解,低头莫语,用意专听。上座讲筵,听众宣扬,普皆闻法,不事在(再)作一个问法之人。
校注:在,应读作“再”,或为“作”之误字而衍。不事:不可。
按,“再”之校无关句意。“不事”是“不用”义,而无“不可”义。全句有七个四字句,中间夹了一个六字句、一个三字句,当有误。上座**,听众又同时“宣扬”什么呢?校注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全句宜校成:“……听讲时光,若汝不解,低头莫语,用意专听。上座讲演,听众喧嚷,普即问法,不是作一个闻法之人。”主旨是:听众是来闻法的,而不应像你一样,以喧嚷问法来捣乱。这是写道安被远公问难不会解答,而强词夺理。作者此处刻画人物,文笔细致。“若”误为“昔”而当作“惜”,又加“可”以足意。
264-17阇梨去就,也是一个志書僧。
校注:那个生僻字或者“卢”或是“肤”的俗字。但“卢僧”、“肤僧”均费解。疑它是“僧”之误抄而未涂去者。
按,“志道僧”是“有志于佛道的僧”,是赞语。而文意却另是远公“遥指道安,怒声责曰”。今议是揭露他是“一个亡道庸僧’。亡道,即不学无术。亡,欲音误为“忘’,而实际形误为“志那个怪字是“庸”字之误。
264-18我乃是人,岂得不合闻法?
按,“闻”是“问”之误。远公针对道安指责他不应问只应听而再作反问。
265-2不见药王菩萨,皆标四时,五果桃李,皆从八节,因地而生。《药草喻》中,分明乃说大根大树,大枝大叶,各著根基,因地而所有。
按,此段要说明各种药草、树木平等接受雨露,遍地皆生,以比喻一切人听法、学法的平等。所以两处“因地”是“应地”之误。又,“五果桃李”怎会同“药王菩萨”对言?“药王菩萨”又怎会“皆标四时”?当由“药旺普生”成误。
265-5遂揽典尺,抛在一边。
项楚文:“‘典尺’无注,不可解,‘典’字应是‘界’字形误。‘界尺’是用以镇压书纸的尺状物。……佛教说法传戒时亦有‘戒尺’,用以敲击发声,以警觉大众。”明说是“界”字之误,实际上又转换为“戒”字之误了。既要“抛在一边”,为什么又先要“揽”到近旁呢?此另议,似为“遂斥典揽”之误。斥,推开、排除义。典揽,经典之要义,此指讲经的讲稿、提纲之类。表现道安气急败坏,连讲稿都摔了。
265-6汝岂不闻道:“斗不着底,死亦难当。”岂缘一鼠之愆,劳发千均之弩。
校注:“斗不着底,死亦难当”当为俗谚,表示斗竞之无谓,永无休止之时。
按,“死亦难当”与“永无休止”并不同义。今议“底”是“敌”字误。言与低水平的人相斗,即令战胜而杀了他,也不值得。敌,势均力敌。道安为自己不能取胜,巧作遁辞遮羞。
265-7汝若见吾之鼓,不辞对答往来。鹪鹩共鹏鸟如(而)同飞,对汝虚抛气力。解事低头旲语,用心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