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果小说>大漠宠妃 > 第37章 纹花刺客(第1页)
第37章 纹花刺客(第1页)
按照烟江纪年这一年是木曜年,总是大雨滂沱的一年。苏弛站在烟江都城的城墙上眺望远处烟雨里的世界,很苍茫也很模糊。他抖抖肩戴正了斗笠,然后理了理湿漉漉的蓑衣。最近的天气格外得怪,祭司们交头接嚷地议论说是赤那神发怒了,命令水神一直不停地跳动着降水的舞步。更多的人私下里说,这是赤那神在发泄着他的不满,不满意烟江王苏沪立苏泽夜为烟江的世子。
十三年前有场同样持续好几天的大雨,那一年烟江王苏沪迎娶牧民的女儿卡瑞娜做他的王妃,赤那神是反对的,于是降下大雨来惩罚烟江王,而烟江王的臣民们也随之被惩罚。那场瓢泼的大雨接连不断地冲击着烟江的土地,洪灾泛滥,像是末日。
可是苏弛从来不相信什么神鬼末日,那些不是人的东西苏弛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苏弛想他们一定是不存在的,人们把它们当做信仰,只是在心里畏惧时寄托信念的一种东西而已。可是现在苏弛同意祭司们的看法,因为他反对那个叫做苏泽夜的孩子自己的侄子成为烟江的世子,他觉得把先辈们好几百年建立起来的部落交给那个孩子是不妥的,因为孩子很懦弱,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苏弛不允许有人把自己家族百年来的基业给断送了,所以他找来许多人到处谣传赤那神不允许苏泽夜成为世子的话。
“大汗王做得很快,”白风尘站在苏弛的身后,也是一身南疆渔翁们的打扮着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饕餮血侯已经在大秦的祭司叶勋的带领下离开烟江了,现在烟江王苏沪是个空有权力的人,整个都城里的邦民都在诚惶诚恐地议论着这件事,他们害怕赤那神将灾难带给烟江,可是他们同时也害怕烟江王会像十三年前那样,把反对他的人一个个都送到赤那神身边,这群愚昧的人很可笑啊。”
苏弛看着遥远的浑浊天空,默不作声。
“大汗王是在想如果赤那神真的存在的话,”白风尘上前一步伸出手接着从天而坠的雨花,“那么他或许会停下这场雨吧?虽说是懦弱的孩子,可是骨子里流着的,是苏家的血液对吧?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却不吭不哭的,不是真的懦弱对吧?大汗王,你的心在犹豫了,那么大秦的皇帝是不会继续支持你的。”
“没有那么想啊,”苏弛绕开话题说,“没有那么想的,我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君临这个天下,那么这个天下到处都是战争的硝烟吧?想要再听见这雨声,可是很不容易了。那一天我希望它很遥远,可是我又希望它快一点到来,你听听这雨声,是不是心里面感到格外的惶恐?惶恐的像是草在疯长。”
白风尘转过身看着满目愁伤的苏弛,烟江的大汗王,烟江王苏沪的弟弟。真是虎一般的人,可是这只老虎在他不该惆怅的时候惆怅了,于是白风尘也跟着惆怅起来,最后两个人都在他们不该惆怅的时候惆怅了,“不过即便是大秦的皇帝不支持你,我们纹花的刺客,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你,为了与你的约定,我们甘愿与这个世界为敌。”
“能给个理由么?”苏弛看着白风尘浑浊的眼,这么问。
“理由是没有理由,”白风尘避开苏弛咄咄的目光,“我们刺客不像你们,总是权谋这个权谋那个,到最后变来变去不知道偏离到那个地方去,凡是我们认定的决定的,我们便会一直坚持下去。我期待看到你许诺的那个时代,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那一天。”
苏弛不知道白风尘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从白风尘的眼里看不出任何东西,他只知道那双眼是历经了无数风霜雕刻出来的,像是寻找猎物的漠北苍狼,没有一丝感情包含在眼里。他想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看尽人世间的繁华寥落,他以前想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归隐于山林的世外真人,可是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怎样的人才算是世外真人。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外真人的。
“大汗王的队伍不只有我们一个的,”白风尘的语气一转,“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无数的人效命于大汗王,那个时候大汗王就不是大汗王了,是这个世界的赤那神,那个时候一切都属于你,而我们这些帮助你达到你心愿的人,所希望的只有看到你许诺给我们的时代而已。”
“那样的时代,”苏弛沉思,“需要我们牺牲无数的东西吧?有的时候我看着烟江的都城沉默在黄昏里的时候,就会想有一天我也走到了我生命的黄昏,然后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永远留在原地打转转。其实这样的时代也好,虽然自欺欺人,可是大家有的仗打,有的饭吃、有的人恨、有的人爱,也是很不错的事吧?但是也是这样的时代,让每个人都被逼上了自己所不愿踏上的路,真是悲哀啊,对吧?”
白风尘看着苏弛,他主动迎上了苏弛的目光,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以大秦使者出使烟江的时候,那一年烟江王还没有把王位传给苏沪,苏弛也只是个躲在他阿妈后面瞄看他的孩子。但是也就是那个孩子的眼神让身为刺客拥有敏锐神经的白风尘捕捉到了,“是个虎一般的孩子,”那个时候他跟随从说,“这样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可是现在,长大后的苏弛再也不是但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幼虎了,他的心变得逐渐坚强起来,坚强的让人生畏。
他所见到过的王族贵裔,无不是整日风花雪月信口胡侃的人,自以为领略万千风骚诗词赋无人能及,每天写写感伤的诗歌叫人作谱哼唱,却不懂得去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白风尘想到这里就笑了起来,苏弛看着他,像是看着一个老顽童。白风尘花白的发间有东西蠕动着,那是他引以为荣的东西或者小家伙,是只蝎子,极西之地的蝎子王,用毒的刺客喜欢从小捉来幼儿期的蝎子王来驯养,然后用尽办法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杀人工具。蝎子王的毒,至今似乎没有哪一位神医解得开。
“不知道大汗王听没听过大秦神武皇帝的故事,”白风尘忽然说,“那个亲手杀害了他七个哥哥威逼父亲把皇位传给他的人。”
“我知道他,”苏弛说,他从小就在听阿妈讲那个男人的故事,父王也偶尔提到过,“我阿妈以前跟我说,在他之前是没有皇帝一说的,从他以后各国的君主都下皇命自诩为皇帝,可是真正的皇帝,也只有那个男人一个人吧?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他,我在无数个梦里梦见自己成为了他,率领无数兵马攻城略池,把自己手里的刀剑插在每一个自己君临的地方。”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他究竟是一个如何的人,”白风尘打断苏弛的话,“大秦神武皇帝立下成为皇帝垂足青史的决心时,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只有很少的支持者,皇宫里的七千御林军而已,可是他还是做到了。他率领御林军杀害了他的哥哥们,然后提着他哥哥的人头到老国主的面前威吓老国主要老国主把皇位传给他,想想如果始皇帝没有那么大的勇气的话,他不过只是个碌碌无为中庸的八阿哥而已,哪里轮得到他成为大秦的皇帝?可是他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他希望自己留给历史的,不是历史安排给他的人生,他要用自己的手改写历史,然后把自己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最后他做到了,因为他的信念。虽然他弑兄逼父,可是到今天,谁又在讨论他成为皇帝前的故事呢?一个人在他最耀眼的时候往往是无人看得到的,历史在回头描述他的时候,只是几句话而已,然后留给后人们去拜读去遥想,但是数百年前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真实的故事呢?”
“阁下的意思是?”苏弛实在搞不懂白风尘想要告诉他些什么。
白风尘昂起头来,“我率领白氏一族最优秀的秘党纹花刺客来支持大汗王,为的就是跟大汗王讲明一件事,想要拥有这个天下的人必须是最勇敢最坚强的人,因为拥有这个天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是个没有人知道结局的赌博。如果你没有那么坚强那么勇敢,我劝大汗王还是放弃吧,把烟江的王位留给那个孩子,然后再让那个孩子把烟江的王位留给他的孩子,就这么一代代下去,像大汗王说的,大家有的仗打,有的饭吃、有的人恨、有的人爱,也是很不错的事。所以说大汗王要明白,在拥有天下前成为烟江的王,值不值得大汗王为此甘愿牺牲一切?”
“我不懂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坚强勇敢的人?”苏弛说。
“所谓最勇敢最坚强的人,”白风尘垂下头来,“心都是狠的,没有什么能让它改变它的跳动速度,大汗王明白么?你要成为烟江的王,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拿下苏沪父子的首级。在此之后,不仅仅只是白氏一族,大秦的十万饕餮血侯将和你一起驰骋这个天下,魔君的后裔将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被抹杀,我们四大家族的宿命结束,你们这些帝王获得权和力,是很好的交易。”
“这样啊,”苏弛也低下了他的头来,“我知道的。”
是个心里面强大的人啊,白风尘跟自己说,他压低了斗笠让雨水顺着斗笠滑落。苏弛形容这场雨的话很形象,也很具体。这样的雨声让人听了后心里真的会发慌,像是荒草在拔节儿地疯长。
“这是我的命,”过了很久,苏弛这么说,“我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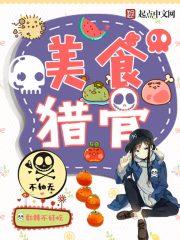
![维密天使[综英美/美娱]](/img/154274.jpg)
